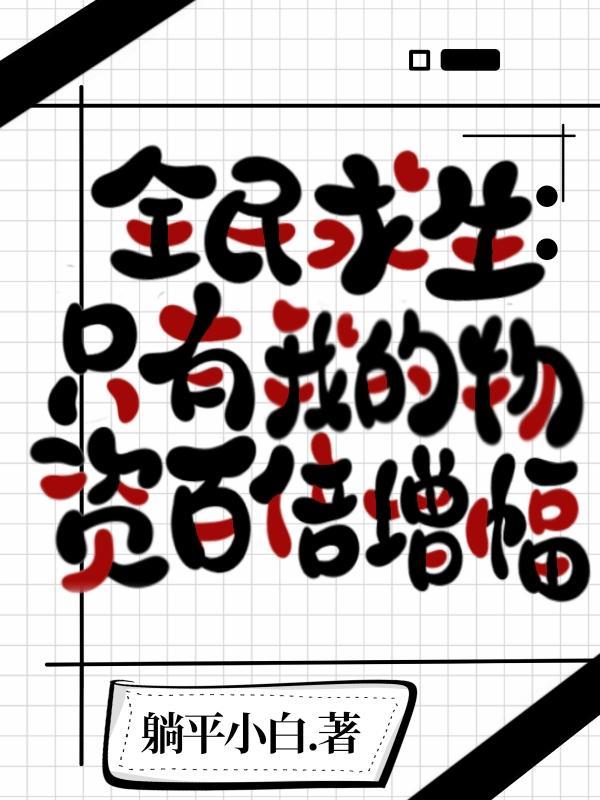69书吧>日月重光全文免费阅读 > 第177页(第2页)
第177页(第2页)
到了宫门,就见崔骥征站在一极大青纱马车之外,周遭还有十几骑锦衣卫扈从。
“你们俩都上车。”
朱厚炜的声音从车内传来。
二人上了车,崔骥征忍不住笑道:“陛下原先那象辂竟还留着,只换了个壳。”
朱厚炜也笑,“让你旧梦重温。”
案上有糕点茶水,朱载垠自觉地给两位长辈都倒了茶,就听崔骥征道:“如今咱们殿下可厉害了,竟一眼看出楚王世子不似善人,还提点我留意呢。”
“是么?”
朱厚炜闻言惊喜地看了过来,“咱们载垠长大了。”
“表叔就知道取笑我,”
朱载垠虽有些得意,但也有些不好意思,“所以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烝父妾。”
不知道怎么和这么大的孩子提及敏感问题,朱厚炜有些尴尬。
朱载垠大惊失色,“他把他爹的妾室蒸了?楚王这也能容他?”
崔骥征一口茶水差点吐出去,没好气地看了朱厚炜一眼,“子与母辈淫。乱曰烝,不是放在锅上烹了。”
“这个世子,你们锦衣卫再去查一查,我觉得迟早还会生出事端,要是能起早将他废了,也省得日后生变。”
朱厚炜笑了笑,“湖广最不缺的,便是他们这些殿下。”
崔骥征点头,“你不说,我也会盯着的,有咱们殿下的谕旨呢。”
朱载垠对他这表叔总拿自己取笑的恶味很是无语,“父皇,咱们这是去哪?体察民情?”
崔骥征看看朱厚炜的装束,“难道是登黄鹤楼?”
大名鼎鼎的黄鹤楼几经沧桑,分别在洪武和成化年间由当地官吏修缮,来了江夏,一睹盛景也是合理。
“非也。”
朱厚炜悠悠道,“咱们去汉阳。”
过了半个多时辰,车才稳稳停下,崔骥征刚想下车,朱厚炜却按住他的手,“等等。”
朱载垠看着他取了自己的玉绶将崔骥征的双眼蒙住,牵着他的手下了车。
这时不论是崔骥征还是朱载垠都不知这做法在后世可谓烂俗,彼时的他们只觉浪漫奇。
崔骥征不能视物,凭感觉判定自己此时位置既有山风又有江风,应该是长江岸边的山上。
朱厚炜选了个最好的位置,将玉绶取下,崔骥征缓了缓才将眼睁开,就见一楼依山就势而建,飞檐大脊、粉墙筒瓦,回廊斗拱,颇为雄奇。檐上四角均挂着铜铃,临风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