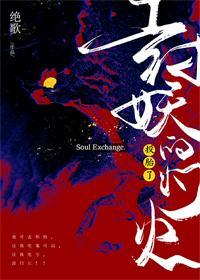69书吧>无家可归后被上神捡回家当夫君了 > 第91章 我既来了就会尽全力救你父亲(第1页)
第91章 我既来了就会尽全力救你父亲(第1页)
最后褚亦棠又是被澜聿牵着回去的。
褚亦棠一路上都在反思,到底是哪里不对,难道是自己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吗?
怎么澜聿的脸皮还和个子一块长啊??
澜聿没要元清给他磕头,长淮只想要拿个彩头,也没要元清磕。
元清泪流满面,痛斥自己心胸狭隘,并约好了回天京后过生辰那日他做东,去贺盛楼好好聚一顿。
晚间的时候二人用过了晚饭就没再出门,来西呈已有两日,后天就得要启程回京。
褚亦棠窝在澜聿怀里看书,腿上还有一袋豌豆酥,边看书边吃。
澜聿一臂环着他,顺带拿文卷,一只手执笔写字,正仰着头看公务,来了西呈也不得闲,累了一大堆公文没批阅。
褚亦棠每看完两页就往后头递一块豌豆酥,澜聿也很默契配合地张嘴接着。
澜聿批完了一本,脖子长期仰着有点酸,他把东西放好就低头去找褚亦棠讨亲。
褚亦棠翻过一页书页,眼睛还停在书上,抽空在澜聿侧脸上亲了口。
补给完毕。
澜聿眼皮子浅,一点肉腥他就满足了。
今夜是寒隐守夜,尚尧和他轮换时,很郑重地对他说了句辛苦了。
褚亦棠事后还是有表扬澜聿的,把他的心肝宝贝从里到外夸了个遍。
澜聿很受用,一对梨涡漂亮的不得了。
但小心眼的祝天上神已经把今天判定为澜聿人生中最后一次抛头露面了。
绝无可能再有下次。
澜聿在马球场跑了一下午,睡觉的时候是褚亦棠哄着他睡的。
夜已幽深,万籁俱静,帐外却有人在敲着帘子。
寒隐也没敢高声,也不能擅自入内,但澜聿眠浅,寒隐第一下敲帘他就醒了。
澜聿轻声下床掀帘,眉目倦懒。
“何事?”
褚亦棠迷糊间翻了个身,还不甚清明,帐子中昏黑一片,澜聿从外头进来就去衣架上拿外袍,褚亦棠听到动静,从被子中支起身,皱了皱眉:
“去哪里啊?”
澜聿以为是吵着他了,草草穿了外衣,钻进床帐里,握住褚亦棠的手,脸色不太好看,纠结片刻才开口:
“元清的父亲出事了。”
本该是夜深人静时分,元戊帐中却挤满了人,此趟随行西呈的医官都聚在屏风前,屏风后,院使正在给元戊把着脉,面色凝重。
神帝与魏巍也在帐中,元戊事突然,被现时就已危在旦夕了,院使给他强行服用了续命的丹药,又施针封住他几处要脉,才算从悬崖边上抢回了一条命。
院使把完了脉,从屏风后绕出,众人立即围绕上前,元清红着眼,手抖得不像样子。
院使只无力地摇摇头,拱手道:
“回禀陛下,元将军是中毒不错,可此毒毒性甚烈,只一炷香时间即可侵入肺腑,药石难医,若不是元将军修为深厚,若换做一般人,此刻已然是一滩脓水了!”
“臣见识浅薄,此毒闻所未闻,解毒之法难求不说,更需时间!可元将军已然是强弩之末,撑不了多久了,再拖下去,恐回天乏术啊陛下!”
听完院使的话,元清只觉眼前一阵阵地昏,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他几近跪倒在地,痛苦地以手掩面,无法自抑的痛哭声自掌中撕心裂肺地传出。
弘燃红着眼眶,一下一下地拍着元清,也很无措,他无法想象若是他的父亲此时也躺在病榻上生死难料,他会不会比元清还要崩溃。
神帝不忍去看,他鼻中酸楚,强忍要落泪的冲动,沉声道:
“可还有其他的法子?你在京中多年,寡人最信得过你,只要救得活元将军,要什么你尽管开口!寡人就是寻遍三界也给你找来!”
院使踌躇,正要解释他并非不尽力,而是元戊已医药罔效时,帐外就传了人声来。
澜聿携着褚亦棠进到帐中,听见元清的哭声,澜聿心中一沉。
寒隐说毒时元将军就已无力回天了,院使吊着他的命,也只是一息尚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