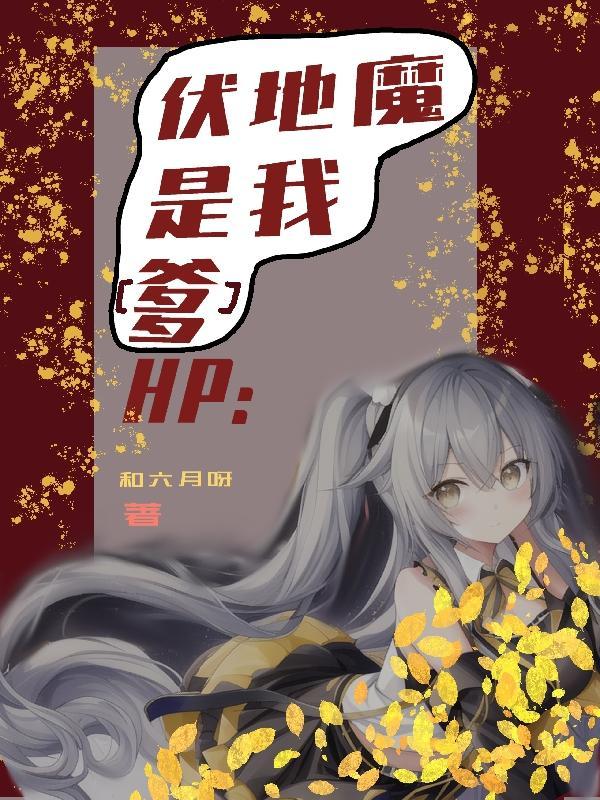69书吧>与秋书歌词 > 第16节(第2页)
第16节(第2页)
吴虞问:“在哪?”
季时秋回:“没问。”
吴虞说:“远了不去,不舒服,走不动。”
季时秋看她几秒,弯身拉开床头柜抽屉,翻找之前自己用过的水银体温计。
吴虞看出来了,问:“你找温度计?”
季时秋应:“嗯。”
吴虞说:“我还给林姐了。”
季时秋转身要离房,被吴虞叫停,她勾一勾手,斜挨在床边:“你给我量。”
季时秋一顿,从床尾绕到她身侧,俯身要用手背探她额头。
吴虞伸出一根手指,隔开他。
“用你的额头,给我测。”
她幽静地看着他,轻佻但诱人。
季时秋沉默。喉结滑动一下,他单手按住床板,另只手握高她脸,与她额头相抵。
呼吸交错,四目打结,他无心狎昵,很认真地贴了又贴,再三确认。
两人的温度几乎一致。
极近的距离里,女人忽如恶作剧得逞,吃吃笑起来,气息喷洒在他鼻头。
额离开额,但他的唇贴住她的,衔住她肆无忌惮的笑花儿,又渡回去。
吴虞的喘息迷乱起来,手臂勾缠住他,再不放开。
季时秋猜到她装病,但他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吴虞本就是随心所欲的人,一秒一个主意并不意外。
至于他,负责兑现自己的承诺就好了,用每一个现在陪她冒险。
其他的,他不敢想,或哄骗和宽解自己应该来得没那么快。
绥秀村挨家挨户都有桂花树,有金桂也有丹桂。
丹桂花色偏橘红,而金桂是柠檬黄,林姐屋后栽种的,是最常见的金桂,两株挨在一处,花粒攒聚在黛绿色的枝叶间,显得羞答答,但走近又觉花朵太大方,香气浓郁到不讲道理,蜜一般淌出来,不由分说地将每位树下人裹入浓金色的馥郁。
“上学那会最喜欢桂花,”
吴虞双手插在裤兜里,仰头看花叶间那些若隐若现的光晕:“其他花,存在感都没这么强。”
林姐正往草泥地上铺闲置的床单,用于纳落花:“桃花不是花?月季不是花?哪个花不比桂花显眼。”
吴虞并不赞同。
在她看来,没有花能如桂花般,未见花貌仅凭气味,就那么明晰和昭彰地告诉她,秋时已至。
林姐嫌吴虞碍事,叫她站旁边去,接而举高竹竿,教季时秋怎么敲花枝。
季时秋却摇头:“不用,我以前在家弄过。”
吴虞说:“小时候骑树上摇的么?”
季时秋无语地看她一眼。
他不吭声,挽高袖口,接了竹竿专心挥打花枝。桂花雨簌簌落下,很快往床单上敷了层淡金色的薄香雪。
林姐观看片刻,满意离去,她要去鸡舍喂饲料收鸡蛋,就让他们先敲着。
再回来,不想吴虞已大喇喇躺在床单上,惬意地眯着眼,任明媚的花屑与光点散了满身满脸。
而打花人跟没瞧见似的,自顾自打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