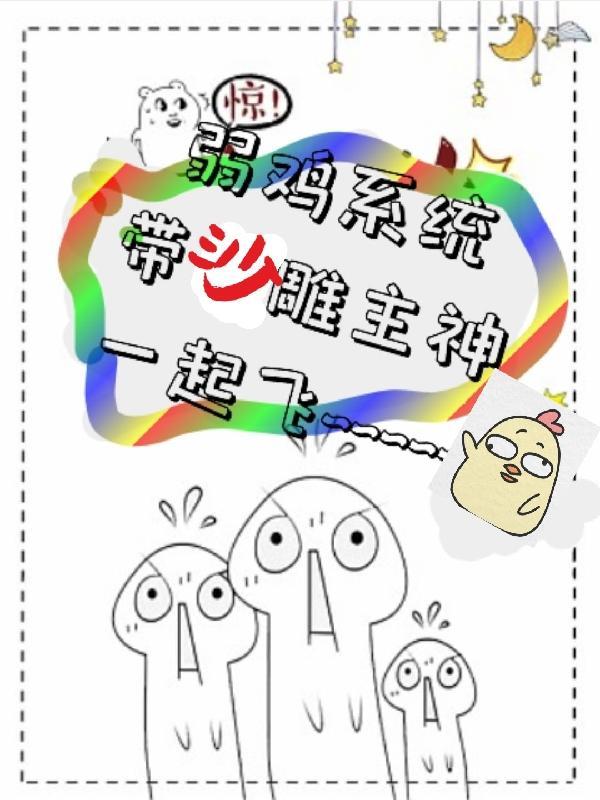69书吧>流年照锦 钓鱼养猫 > 第187页(第1页)
第187页(第1页)
谢锦伸手拧住她的一边脸颊,带着三分威胁道:“不要说什么弥补不弥补了,阿爹说已有好些朝臣回头上朝,你却不给人家留位置了?
这些任性还是收起来为好,赵家党羽虽多,也不是都做过坏事,得饶人处且饶人,既能得一个宽宏名声,也能让阿爹少费些心。”
“对于赵家人及其党羽,我的确是有想要一网打尽的意思,不过既然岳父和你告了状,我自然还是要给他些面子。”
姜照不情不愿地开了口。
她是记仇,更是想要震慑,省得一个赵家倒了后面再出现别的赵家。
但谢玉折的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虽然姜照手底下的人足够用,但多数都是初出茅庐,自然没有那些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滑头用着顺手。
姜照松了口,次日就下了几道圣旨,让一些及时回头表忠心,又与赵家实际牵连不大的大臣官复原职,顺便正式把谢玉折提回了吏部尚书之位。
至于另一个难搞的秦相,林观现身宫中祭典足以表明他对今上的认可,也直接象征了天下文人归心,作为他亲传弟子的右相秦端,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而在秦相犹豫未定之时,姜照又亲口向他保证,虽然自己不打算纳夫生子,但也不会布告天下册封谢锦为后,逼着文武百官和天下人去称一声千岁。
秦端沉思片刻,长叹一口气,终于妥协。
于是随着嘉平三年冬日,京都的第一场大雪落下之时,由姜照自己挑起来的群臣罢朝事件终于悄无声息地走到了终点,整个朝局也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姜照打算年后再清算赵家,暂时也没有对赵恒则做出什么处理,但他一病不起,空负左相之名,却已有许久不曾上朝了。
十二月中旬,年关愈近,戍守大孟与南蛮边界克阳关的将领6珂接到了皇帝密函,突袭南蛮边境,主动起进攻,这场避无可避的战事,终于正式击响了战鼓。
几乎每一日都有最消息传到宫里,或是捷报,或是请旨,或是单纯陈述战事,虽然最后落的是6珂印信,但是那些熟悉的字迹和陈词,一看就是出自6苍玉手下。
姜照的心彻底定了下来。
虽然她没有直说,但满朝已无人不知,所谓关在天牢等候落的6大元帅,早已不知何时跑到了边关造势,这舅甥俩一心对外,压根儿也看不出什么有了隔阂的样子。
而因战事未停,宫中年宴也少了丝竹管弦、歌舞升平。
姜照本来打算带谢锦出席,但被她婉拒了,毕竟她心知肚明,群臣现在的不反对只是屈从于无奈,而并非是从心里接纳她,她也实在没必要去找什么不痛快。
于是这份不痛快就给了姜照,谢锦与康王妃一起领着姜晗,在熙和宫与姜溪、青时姑姑以及元祥等人在一块儿,也算是过了个热热闹闹的年。
姜晗年幼,熬不住夜,很快在娘亲怀里睡去,康王妃搂着她不舍得撒手,谢锦就做主让人收拾了她从前住过的那间偏殿,让王妃带着姜晗留宿了。
临近子时,姜照的御驾才回了寝宫。
所有的热闹皆已散去,谢锦坐在灯下绣花,金豆打着呼噜趴在她脚边,听闻动静声格外敏锐地抬起头来探看,瞧见是熟悉的人之后,才又趴回了原来位置。
姜照饮了些酒,面色酡红,眯着眼看向那只疑神疑鬼的小狸奴,过去伸脚赶它走,小狸奴炸起毛来,伸出前爪不断扑打着她的衣摆。
“你又闹它做什么?”
谢锦听见动静,放下绣品将金豆抱起在怀里安抚,不太高兴地瞪了姜照一眼。
姜照扁着嘴走到龙床边坐下,哼哼唧唧地嚷嚷头痛,时不时拿眼瞥向谢锦,见她看过来,又迅收回目光,趴伏着身子把脑袋往被子里埋。
谢锦无奈,矮身将金豆放走,倒了杯热茶走过去坐在她身侧。
“少装模作样了,明儿一早还有祭祀大典,快去洗漱更衣就寝,不要耽搁时间。”
伸手拍了拍姜照,姜照又道:“我和王妃约好了,明日带阿圆出趟宫,去护国寺祈福,然后我回谢家陪爹娘过年,过几日再回宫里来。”
话音刚落,姜照猛然把埋进被子里的脑袋拔了出来,露出格外委屈的神色,“不陪我赴年宴,不陪我去祭祖,还要把我一个人扔在宫里?”
谢锦不吃她这一套,把手中的茶盏塞给她,淡淡道:“我平时也不怎么出宫,趁着过年尽尽孝心不是应当?况且也去不了几天。”
姜照又要说话,被谢锦伸手捂住了嘴,“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也不要胡搅蛮缠,省得我阿爹又要对你有意见了。你自己收拾一下,我去给你打水来,洗漱完就歇了罢。”
说完就起身出了殿门,留下姜照一个人捧着茶盏生闷气。
次日年祭祀大典,姜照起得早,谢锦也不晚。
她们收拾的时候康王妃带着姜晗来给姜照请安,清元殿那边一早送来了衣,姜晗穿一身红色,衬得一张圆乎乎的小脸儿喜气洋洋,康王妃都忍不住说:“这孩子被陛下养得很好。”
“是锦娘的功劳,她比朕心细,和晗儿相处的也好,皇婶也该放心了。”
姜照被宫人们伺候着穿上厚重华丽的冕服,更显得沉稳庄重许多,单是坐在那儿,纵是神情和缓,亦有不怒自威的气势,令人不敢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