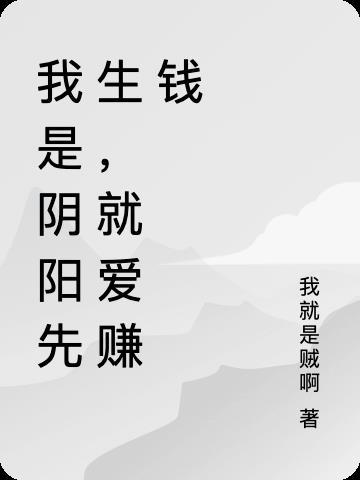69书吧>哪只鸟最厉害 > 第79頁(第1页)
第79頁(第1页)
倪謹盤腿坐在床上,感受著苦味和甜味交融著在舌尖化開,心裡琢磨著要把陳姨給她的一大包奶糖分一半給小藍哥哥。
她正把那巧克力包裝紙在手上疊了又疊,房門被咚咚敲了兩下。
「哥!」倪謹立刻下床,「你去哪了!我早醒了。」
倪諍提著一碗小餛飩進來了。他看了眼頭髮亂蓬蓬的倪謹,將那小餛飩擱在床頭柜上:「刷牙洗臉了沒?洗完吃早飯。」
「哥哥你吃過啦?」倪謹抓住他的胳膊,「哥,我想把我的奶糖送給小藍哥哥,你今天去找他的時候能不能帶我一起去?」
「……」
倪諍沉默了一會兒才摸摸她的腦袋道:「小藍哥哥回家了。」
「回家了?」
「嗯,回蕎城了。」
倪謹瞪大了迷茫的眼睛。她想藍焉大概是有什麼急事,才這麼突然就回家。可回家不代表他就不會再來野水,自己為什麼會有壓不住的失落感?
「那,那他什麼時候再來?」她小心翼翼地問。
又是沉默。倪謹覺得哥哥這兩天很怪,問什麼都不回答,或是模稜兩可地將問題帶過去。哥哥不是這樣的,哥哥明明坦率、誠實,從來就是有問必答的。
她看見倪諍脖子上掛著條吊墜。吊繩材質是棕色的蠟皮繩,綴了些合金配飾,底下串著一個小小的木塊。
她無暇去思考吊墜是從哪來的,只是執拗地盯住哥哥的眼睛,等著他開口說些什麼。
沉默沒有維持太久。倪諍忽然蹲下來,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扶著她的肩膀說:「那個奶糖……你就自己留著吃,好嗎?」
倪謹鬧了兩天脾氣。
她不肯吃東西,報復似的熬夜看動畫片。無數遍地問,小藍哥哥還會不會回來,為什麼不回來了,得到的只有一如既往的沉默。
不是結了婚的嗎?不是要永遠在一塊的嗎?哪怕,哪怕是……過家家一般的玩笑,可那天她把紅裙子蓋到藍焉頭上、那兩人在她面前緊緊牽住手的時候,她幾乎要以為這是真的。
這一切是真的。他們會像家人一樣永遠待在一起。
可藍焉飛走了。
倪謹想起藍焉和自己說的「換種方式飛」,難道他指的就是這樣離開嗎?
倪諍拿她沒辦法,最後乾脆不再管她,開始不聞不問,由了她去。這下倪謹才有些慌了,生怕哥哥再也不關心自己,眼睛眨巴眨巴著又湊上去。
兩人心照不宣地沒再提起過藍焉。
倪謹有時希望哥哥是在開玩笑,小藍哥哥只是回家一趟,多的是機會再來野水。可這分明是無望的幻想,因為從那天起,她再沒見過藍焉。
沈寺考上了北方的大學,八月底將要動身離開野水。他問倪諍將來有什麼打算,真的準備在野水開一輩子的音像店?倪諍笑笑不作答。
他們正坐在馮郴的茶館裡,各拿著一根老冰棍。
「我說,」沈寺撕開冰棍包裝袋,「我以後指定是不會待在野水了。我叔讓我既然出去了就好好學,以後在外面也像他一樣干出一番事業來。」
他拿肩膀撞了下倪諍:「那就留你一個在野水?」
「不是還有小謹嗎。」
「別扯了,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沈寺說著沉默了片刻,「我可拿你當最好的朋友,以後我們都往外跑不回來了,那你也出去不好嗎?」
哪有這麼容易?倪諍想。他要留在這裡,要負起該負的責任,守著爸爸媽媽留下來的店,守著……守著那片還未被開發的舊球場。他有什麼可出去的?他活該被困在這裡。哪怕一輩子也活該。
趙秋池和馮郴也準備去蕎城創業了,沈志遠給的資金。前陣子連在蕎城的房子都找好了,這兩天才告訴他們。看得出來這兩人很幸福,將要一頭扎進充滿希望的未來去。趙秋池問倪諍要不要跟著一起,被他搖搖頭拒絕。
「你倒是無所謂了。」沈寺清楚他心裡在想些什麼,「我還不知道你,你就自暴自棄吧,覺得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找不到向上的動力,是不是?那你想過你妹嗎?」
他忿忿地吮了口冰棍:「你想過小謹嗎?你在這兒把自己一輩子賠進去,小謹也跟著你一起?她多聰明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這麼說也不怕你不高興,你在這兒就是給不了她最好的。野水有點小錢的都把孩子送出去上學了,還有那些五花八門的興班,學這個學那個的,你就真的一點都不想讓小謹也有?」
倪諍非常不想承認,可這話確確實實刺痛了他。
倪謹想要的鋼琴,也一直沒買成呢。
「你沒什麼可顧忌的啊,什麼都不是事兒,都是可以丟在身後的事兒。」沈寺醉了酒一樣搖頭晃腦,「我說真的,你還顧慮什麼?倪諭?你傻不傻,這不正好是遠離他的機會!我看藍焉是沒說錯,狠不下心來也是種軟弱。」
他越發恨鐵不成鋼起來:「你認真想想我說的話,我沒說錯吧?離開野水,離開這個……傷心地。什麼都能留在這裡,一切好的不好的,只要你想丟,就能丟掉。」
「只要我想丟……?」倪諍愣愣地重複。
離開野水,所有傷心都能留在這裡嗎?晦暗的舊夢能丟嗎?徒勞的無望能丟嗎?日復一日的心灰意冷能丟嗎?
他沒用的、害了人的愛,能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