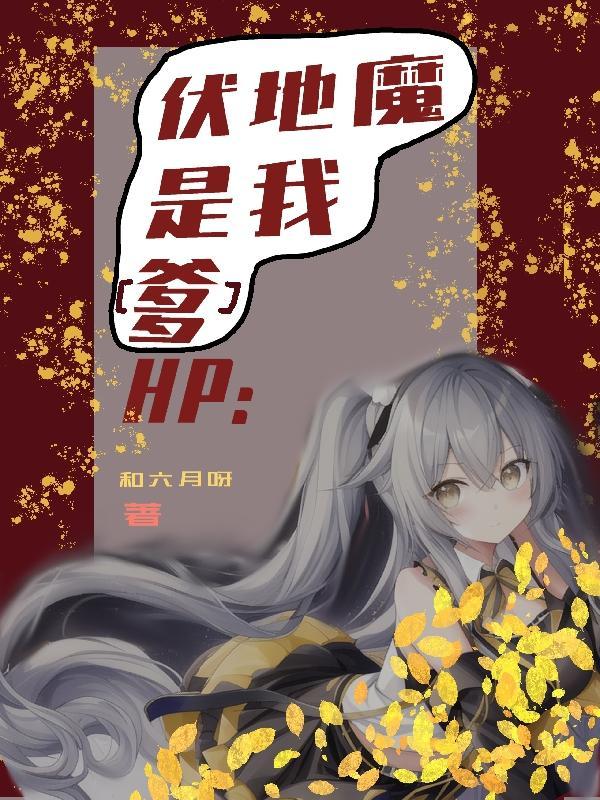69书吧>吸血的鬼魂by > 第100页(第1页)
第100页(第1页)
她看了我一眼,似乎猜测着我这话里的意思:没有啊。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你的话里。我顿了顿,道,是不是他老是想要你的身体?
她的脸一下红了。我说得那么赤裸裸的,她也有点不好意思吧。
你这人。。。。。。你这人怎么这么想。人家很正人君子的,连手都不太碰我,哪象你,满脑子的脏东西。
门关着,外面有个秘书,不过屋子是隔音的。。。。。。患者强奸女医生,那不算太离奇的闻吧。是不是值得。。。。。。
你想什么呢?
她的话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我身上一凛,有点尴尬地笑道:有点想困了。
她皱了皱眉头,道:是啊,我有点跑题了。今天给你打五折吧。
还要钱?
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但不是无偿的。
我的喉咙口出了一声干笑,坐了起来,道:那还有别的服务么?
她看着我,惊恐地说:你要做什么?别乱来!
我向她逼近,嘴里挤出几声干笑。我有点惊愕地现,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种笑声也好象并不是我的。我走上一步,她坐起来,张开嘴,似乎要出尖叫,我猛地一个耳光打在她脸上。她踉跄了几步,人向后倒去,从躺椅上翻下去。在她的脸上,磕出了血来。她大声喊着:来人!来人啊!可是她这病室隔音大概太好了,我记得外面那个秘书也总戴着随身听在听,根本没有人理睬她。
她披头散地从地上爬起来,刚才那种雍容华贵已经一点也不剩,只是显得象一个正在打架的农妇。我走上一步,她惊慌地想冲到办公桌那边,然而我已拦在她身前,她根本没办法走过我。
你想做什么?你放过我吧,别人都知道你进来的,我不告诉别人就是了。
她打量着四周,大概想寻找一件防身的工具,但是她这儿连花瓶也是塑料的,本来就是怕出意外,所以都是很短的一次性原子。她以前也许根本不会想到会有病人攻击她,所以这里一点防备也没有。
我走上一步,她已走到窗子前,没办法再退。她抓着一个塑料花瓶看着窗子,手足无措。她这窗子很大,但却是用八毫米的钢化玻璃做的,就算用铁锤来砸,可能也只能砸出一个白印,别说用这么个塑料花瓶了。我走到她跟前,她用花瓶打了一下我的头,但只是让我觉得象被掸了一下,根本没什么用。我伸出手,抓住她的头。
她的脸上,有些血迹。那些血迹正散出甘甜的腥味,正如诱惑。我把头凑到她脸前,伸出左手的小指刮了刮她的脸,把她脸上的血迹沾了一些下来,放在嘴里。
那是一种何等甘美的味道啊!好象早晨初开的雏菊瓣上正在滚动的露珠,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有了第一次无望的爱情后落下的泪水,象枝头烂熟的葡萄中滴落的如淡紫水晶一般的汁液。那一丝淡淡的腥味有种野性和疯狂,从我的舌尖闪电一般滚落,几乎瞬间融入我的全身,让我每个骨节都开始热。
我把手拂过她的面颊,她的身体也象一枝风中的芦苇一般颤动,象是被捕猎的猛兽盯上了的小食草动物一般一动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凑到了她的颈间。
当我的犬齿正要刺破她的皮肤时,她出了一声凄厉的叫声,手无望地向上拼命抓着。
她的力量本来就与我相差得太远,她的这些动作只是毫无用处的徒劳。我伸手一把抓住她的左手腕,左手揽住她的头,正要咬下去的时候,啪一下,那张窗帘劈头盖脸地掉下来,罩在我头上。
那是她最后的挣扎吧。尽管我和她都被罩在窗帘下了,我却没有一点惊慌,左手仍然用力揽住她的头,右手一把撩开那张厚重的窗帘。
窗帘一移开,外面炽热的阳光一下直射进我的眼。这个季节,这是难得的晴天,和熙的阳光照在每一个地方,象给所有东西都镀上了一层金。外面,人们有的在悠闲散步,有些匆忙走着,每一个人都显得那么健康快活,即使只是表象。可是,阳光照在我身上时,却象刀子在割着我身上的皮肉,让我疼痛不堪。
我在做什么?
我一下放开了她,向后退了一步,伸手看看自己的掌心。我的手掌一般都很红,据说那在相书上叫朱砂掌,算是有福之人。可是现在我的手掌却白得青,毫无血色。
我是怎么了?
也几乎是一瞬间,神智一下回到自己身上。我惊慌失措,蹲了下来。阳光毫不留情地冲刷着我的身体,象有一万把小小的刀子同时刺入皮肉。那种钻心的疼痛里也带着一种狂喜,同样也带着深不可测的忧郁。我抱住头,按捺不住地抽泣着,喃喃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她也许有点慌乱,稍整了一下头,小心地绕开我,走到门边。每走一步,她都紧张地注视着我,也许怕我会暴起伤人,或者突然又把什么扔过来。
走到门边,拉着门,她小心地问我:喂,你怎么了?
我抬起头。这时,我已没有刚才那种古怪的迷乱感觉了。
好象,刚才是魇着了一样。
她也平静下来,道:我给你开瓶安定,你回去吃了睡一觉,明天还是去精神病院看看。
我站起身,走过去。她一下拉开门,跳开了。我看见外面那个正戴着耳机的女秘书有点诧异地向这儿张望。我道:好吧,对不起,请你原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