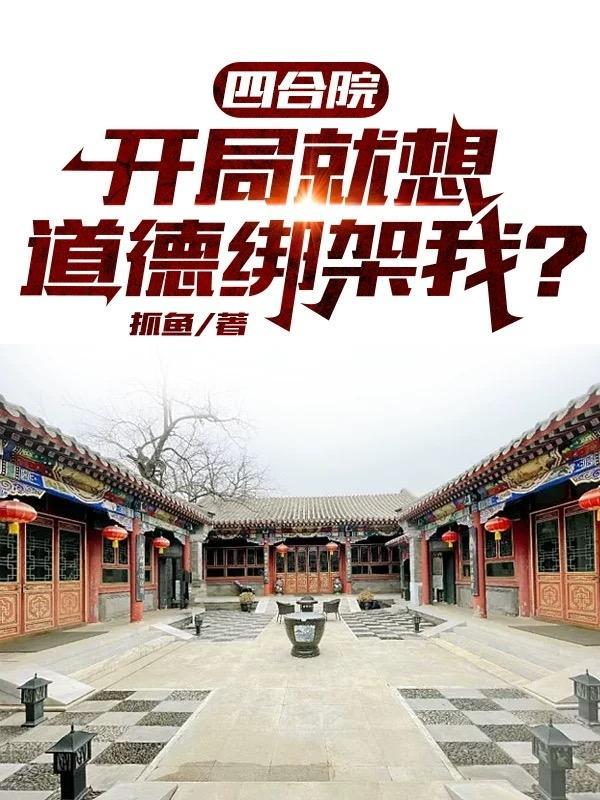69书吧>太后被抓 > 第93章 有人树上一直有人(第1页)
第93章 有人树上一直有人(第1页)
现在看来,潘清儿多少有些活该,她鄙夷地想,贪心的女人总是活不长的,这老鸨已经让她格外另眼相看。
一个女人,处心积虑积攒一切,人脉、权势、财富,哪怕连如今维系的野心,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一个男人。
她想到阿乙,禁不住暗骂愚蠢。
有这样的例子珠玉在前,她定不会在男人堆里绊倒。
说到潘清儿,仿佛和“组织”
颇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女人杀过“组织”
的人,“组织”
却不曾下过以命抵命的指令。
“组织”
曾明令落脚济阳城的各色成员不得与潘清儿生交集与冲突。但每每需要帮助时,那些完美助力的背后总是如影随形地穿插着旖旎阁的影子。
没有杀手会愚蠢到好奇打听这样的事,杀人工具不需要动脑,只需要服从。
阿酒那次如是,这一次如是,她仅仅只是比旁人站得离那女人稍微近过一次,但依然看不透对方所求所愿。
她这次利用旖旎阁为幌子伪造身份,用旖旎阁多年前建造的院落困住了那二人,在旖旎阁的庇护下安然蛰伏了大半年。
自己与潘清儿不需交集,甚至连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都不必,这一切很顺其自然地生了。她们两方不管谁暴露,都不需要担心会留下尾巴出卖对方,彼此都能确保安然。
真不知这到底归功于“组织”
的强大,还是那女人多年筹谋的厉害之处。
她第三次抬头看天空,清亮眸中逐渐积聚起紧张和兴奋。
终于月近中天了!
她努力回想自己适才所有的伪装和准备工作。
她已经在院落必经之道上观察了数天。白天化作卖糍糕的摊贩,晚上与乞丐为伍。
没有官兵经过,没有高手气息。
她将手按在腰间的短刀,杀人并非她的专长,她这次的目的是以最快的度问出所求物什的下落,万一被现,可用现成人质相胁以求脱身。
可一旦如此,她就再没有机会完成“组织”
任务,完不成任务,还是逃不离死。所以死也要将那二人弄到手。
她出今夜的第一个音色,兀自轻轻啧声。
她就像身处危机四伏般,十分谨小慎微地矮下身躯,在脚后跟的平地上找到一个位置按定。这机关就这般大方地摆在眼前,可惜那蠢货刺史偏偏留着这片灌木。
暗色的面巾后露出一抹得意的笑。
几秒后,仿佛从遥远的地底传来沉闷响动,就像野兽的喉咙被困在瓮中般,是无奈低沉的嘶吼,骤然划破院落岑寂。
她无声用嘴型精确地数着时间,响动持续一会,在她的默念倒数中渐渐恢复静寂。
很好,一切正常,现在只需等待即可。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井口,耳朵不放过周遭任何一丝动静。
轻风拂过,树叶安静得宛若陷入黑甜的梦乡。
这是来自那座雪山冷冽干燥的风,竟连叶子都吹不动一片。
什么样的枝桠连风都吹不动?
讽笑刚因胜利临近而漾起在她脸上,随即全身汗毛倏地一炸,她握刀的手指节因过分用力而变得苍白。
风一直没有停歇,她周围的枝桠从头至尾都安静得诡异。
有人!树上一直有人!
从哪里的环节就入了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