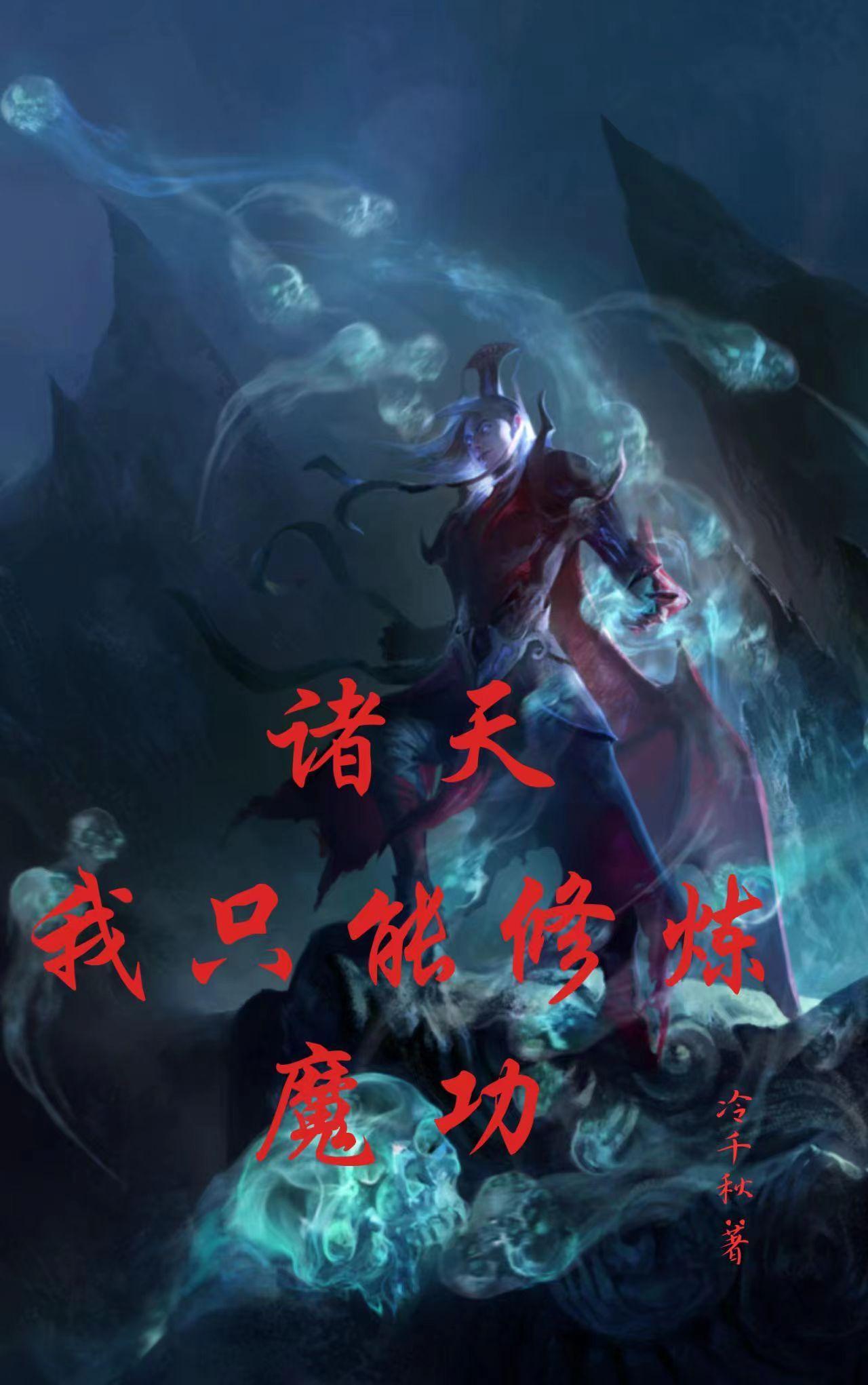69书吧>徐徐简介 > 第86章 冬日(第1页)
第86章 冬日(第1页)
阿史那兄妹启程后,一晃三月,西北路远,北风渐起,便再难得消息,这些时日里侯府事务繁多,操心起来,也算是排遣寂寥,且国事要紧,明容一时也想不起来未婚夫了。
苏元禾在宫里关了月余,听闻晋王和闽王将要启程上京,先前太子之事在长安所掀风浪渐渐平息后,由赵叔元护送着秘密送回侯府,只是不太好在外露面了。
“今冬好像比以往还要冷些,大营里可还要添些棉衣?”
徐光舟刚耍完一套枪,浑身冒着热腾腾的白气,鼻尖红红的。明容捧着手炉,走上前去,苏元禾站在她身后,手里捧着徐光舟的狐裘。
徐光舟看了一眼退仪,退仪会意,接过苏元禾手里的狐裘,披到自家主子身上。
“大营里人多,赶制棉衣还要些时日,先前派去西北的三千人都多带了两身,如今宫里头一时还不出来。”
“那儿更冷些,是该紧着他们用才是。”
明容点了点头,光舟把银枪搁在亭子的柱子旁,退仪端过来一壶热酒,给他饮了一口。
“苏姑娘身子可还好?”
徐光舻坐在亭子里,见苏元禾身形不如从前利落,问了一句。
“牢里挨了些冻,如今还没全缓过来,你倒是眼尖。”
明容坐到他身边。
光舻瞟了一眼苏元禾,看向明容:“人家也不是你的婢女,你就这样舍得大冷天还把她带出来,不是冻坏了没缓过来吗?”
“回二公子,不是姑娘的意思,只是我以往做惯了事,闲不下来,非得让姑娘带着我,就是跑跑腿,心里也觉得踏实些。”
苏元禾屈膝行礼,光舻摆了摆手,她退至一边。
光舟用脚尖一勾,长枪向光舻倒过去,光舻眼疾手快接住,抬头朝大哥颇为不满地皱了皱眉,撅了下嘴。明容扶着头,方才若是躲闪不及,可就要被枪尖戳乱了髻了。
“你这几个月只知去国子学,阿爷教的招式还记得多少?”
“大哥,你是知道我的,我不过能拈弓射箭,于这些刀枪棍棒素来不擅长,阿爷以往教的,到我这里也只是三脚猫功夫罢了。”
光舻把长枪搁在身旁,抚平衣摆,仰头见光舟仍盯着他不放,只好叹了口气,脱了大氅,起身弯腰捡起长枪,捋了捋袖子,走到院子里去。光舟走过去在他方才的位置跪坐下,朝他投来目光。
“二哥明日还要上学呢,昨日方才下过雪,这地上还有积雪,别闪着腰了还是扭着脚了,误了功课。”
明容望向光舟。
光舻站在雪地里,瘦长挺拔,只是光舟那杆枪比他人还高出了不少,显得他有些羸弱,仿佛马上要倒下似的。
“身子骨不硬,进了考场也得扒层皮。”
见光舟态度强硬,明容也不好多说,长兄如父这四个字在他们家体现得淋漓尽致,只好惋惜地看着光舻,让他自求多福。
光舻深吸了口气,一步迈出去,利落起势,激起一片飞雪,高高束起的马尾在脑后随着动作飞扬,长枪向前猛送几次,一个回身,左手离开,右手握住枪杆横扫而过,再回到双手将长枪转得眼花缭乱,周身的雪花也随之飞舞,最后一个收招,站定在原地。
光舟站起身,走到他身边,一脚伸到他胯下带了一下光舻的脚,光舻踉跄了一下,有些懊恼地站稳。
“下盘不稳,便是花拳绣腿了。”
他拿过银枪,抛给退仪,退仪接了枪站到一边去。
“可不敢跟大哥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