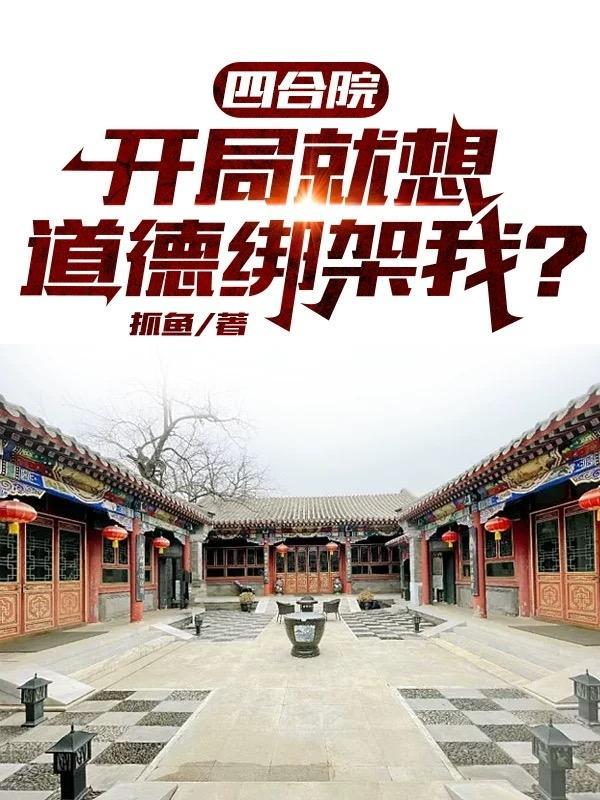69书吧>相由心生的另一句是什么 > 第一章 暗道(第1页)
第一章 暗道(第1页)
“爷爷,这不太可能是王阳明真迹。”
店内古色古香,黄昏的阳光透过门店玻璃,照在老爷子那布满汗珠的脸上,老爷子双手带着白布手套,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着一张严重泛黄的宣纸,视线透过眼镜片,眼珠一动不动盯着宣纸上的字迹。
这张宣纸,不知他从哪淘弄到的,我已经研究多日。
我拿过毛巾帮老爷子擦了擦他脸上汗珠,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报告单,“我担心自己眼力出错,去了趟市博物馆,找王叔用了下仪器,纸是四百多年前的,是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的练七纸,确实是王阳明惯用纸。”
我又拿出了一个变色的测墨试纸,“刮下的墨粉我也测了下,松烟含量不低,符合明代常用的松烟墨特征。”
放下试纸,我也带上了手套,指着宣纸上的六个印鉴,“一个是明代祝续的,他是祝允明的儿子。另外五个都是清代的,有三个找不到,另外两个,一个是袁枚的,一个是钱森的,钱森是袁枚的学生。印鉴总体上也没有问题。”
我手指顺着印鉴下移,落在一行小字上,上面写着:此文至诚也——任坤。
“这个提词,我费了些功夫,非常像是洪秀全的字,任坤也确实是洪秀全早年的名字。”
我又把手指移动到正文处,“是行楷,笔法秀逸、气象雄浑,落笔与收笔习惯,笔划行进次第,都跟王阳明书法无异。”
我直了直腰,叹了口气,“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可是,”
“可是什么。”
老爷子缓缓放下了放大镜和宣纸,从柜台拉出个四脚凳,走到店面前坐下,又从怀中拿出烟斗,吧嗒吧嗒嘬着。
看着老爷子有些不太高兴,我心中一丝窃喜,想不到老爷子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走了过去,“爷爷你有没有注意到文章的落款时间,壬寅年庚戌月,这个时间是1528年11月。”
我有些得意,“王阳明是1529年1月9号去世的,那时候的他,身旁学生众多。而这文章并不是私人书信,所以,如果是真的,就可以算作是王阳明的遗作,王阳明的遗作是无论如何都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的,可我查遍了《见习录》《大学问》《答顾东桥书》等王阳明的全部著作,甚至还翻遍了《明史》的资料,都没有找到这纸上文章的出处。”
我又补充道:“这文章描述的内容风格荒诞怪异,也与王阳明其他文章严重不符。”
老爷子没说话,还在嘬着烟斗,夕阳给烟雾镀上了颜色,随着烟雾的飘动,夕阳也像是跟着在移动,我忽然现老爷子有点心事重重。
“爷爷。”
我有点忐忑,毕竟我这些本事都是老爷子手把手教的,如今老爷子看走了眼,我这番卖弄不会是真伤害到他了吧。
“爷爷你别担心,这文章本身就是古代赝品,还仿力凡,我到时候物色个土老板,准能把它以真迹价格出货。”
“臭小子。”
老爷子有些吃力站起了身,岁月让他的腰背有些佝偻,却仍是高我一头,他拿着烟斗敲了敲我的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老爷子的话停了下来,我连忙问:“什么问题?”
“这个模仿者,所有东西都可以模仿成真的,却为何偏偏要在文风上,留下这么大的破绽让你现。”
我顿时惊住了,缓了好一会,才问道:“您认为这文章真是出自王阳明之手?它是真的?”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既白,也不是非真既假,很多东西,说不清楚啊。”
一声微微叹息传到我耳朵。
此时老爷子已经走到柜台,将那宣纸装进了牛皮纸袋,走出店门,向着家的方向走去。
太阳已经落山,远处街道的大排档出摊了,老爷子蹒跚的背影渐渐消失,我的心情忽然有点沉闷。
从我记事起,老爷子就经营着这家古董店。
应该是受到老爷子的熏陶,我的父亲学的是考古专业,母亲是父亲的同学。
不确定我是受到父母还是老爷子的影响,我也学的考古专业,可我在大三那年却生了场病休学了,休学期间跟老爷子经营着古董生意,渐渐产生了兴趣,也就放弃了学业没再回去。
我的童年,父母陪伴的很少,甚至大多数春节都不能见上一面,当然,他们偶尔从全国各地给我寄来的明信片,一直是我向玩伴们炫耀的本钱。我的人生,基本上都是爷爷和奶奶在照看着,只不过这几年,老两口衰老好像加了一般,腰越来越弯,步履也大不如前。
“周沧,教授去世了,追悼会在6月12号,教授生前给你留了封信,你有时间也过来吧。——陈默。”
一条短信,打断了我思绪,我下意识的看了一眼现在的时间,6月7号。
读完短信,我楞楞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