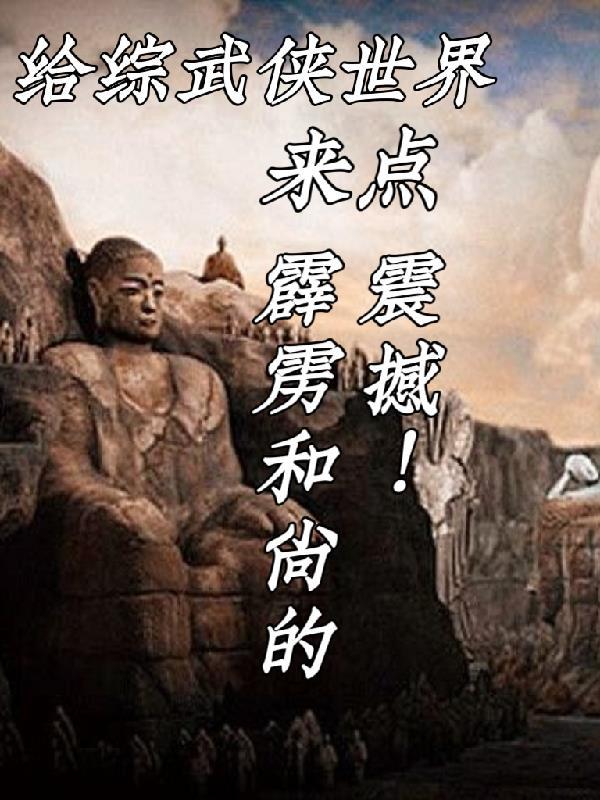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仙尊的遗愿二十章免费阅读 > 第五十章(第2页)
第五十章(第2页)
奚陵低下头,落在地面上的一点,“今天,要下雨了。”
白桁沉默,须臾,沉声说道:“太过重情,太过恋旧,有时是一种负累。”
“听不懂。”
奚陵莫名其妙。
从来没人这样评价过他,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衬得上这样的评价。
就现在想起来的那些记忆而言,他分明应该是个冷情小霸王。
奚陵:“……你为什么又摸我头?”
“抱歉,控制不住。”
嘴上说着抱歉,白桁眼底却看不出丝毫歉意,只有一点带着怜惜的温柔。
“头都弄乱了。”
不自在地躲开,奚陵低声嘟囔着。
白桁:“那我给你重新梳。”
奚陵不答,抿着嘴不理他。
宴会结束已经是深夜了,孙宏茂想要再看一眼奚陵,却现不知何时,山门处已经没有了对方的身影。
他有些遗憾,却也并不意外。
他是玄裕宗的长老,也是奚陵的故友之一,不过奚陵似乎没想起他来,今夜二人唯一的交谈,便是他朝奚陵点了点头,奚陵回了他一个挥手。
也是,虽然勉强算得上故友,但其实当年奚陵站得太高,对外性格又凛若秋霜,严格来讲,两人实在说不上熟络。
微微叹了口气,孙宏茂习惯性理了理衣服,却忽然现,衣服里多了一点什么。
孙宏茂一愣,连忙探入怀中,竟是抽出来了几张薄薄的宣纸。
上面记载的,是并没有文字,全是些动作各异的小人。
这是……一套刀法。
一套狠辣凌厉的刀法。
看得出绘图之人水平相当有限,临时赶制出来的画作粗糙且仓促,但对于在刀法中苦研数百年的孙宏茂来说,已经足够清晰好懂。
独门功法这个东西,几乎每一个修士都是藏着掖着,绝不外传,再亲密的关系也是如此,因着这个原因,纵使孙宏茂曾无数次心痒,想请教请教对方那精妙的刀法,都还是为了避嫌而选择了放弃。
但他没有想到,这样珍贵的东西,有一天会被奚陵以如此云淡风轻的方式交给了自己。
猛地转头,孙宏茂现,不仅仅是他,其他人身上也都有生类似的事情。
大家都有些怔愣,还有几个当场失态的,吓坏了不少年轻弟子。
他们慌乱地想要寻求帮忙,却现就连他们十几年都难得露面一次的太上长老尊胜老祖,都顶着一头花白的头,许久许久怔愣不言。
他手
里拿了一张黄了的画。
其上,
画了一个老人,
和六个小辈。
回到危宿峰时,玄裕宗果然下起了大雨。
白桁回自己的落脚地休息去了,奚陵顶着重新变得整齐的型,坐在窗前静悄悄看雨。
因为有风的缘故,奚陵不可避免地被打湿了一点,余顺给他倒了杯热茶,坐在了另一侧陪他。
这两年里,在危宿峰各种各样的角落呆,已然成了奚陵的习惯,余顺只要有空,便会陪他一起,因而比起主仆,他们的关系有时更像是朋友。
余顺:“玄裕宗很少下这么大的雨。”
淅淅沥沥的雨声之间,余顺探出手,任凭雨水在他掌心积成了一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