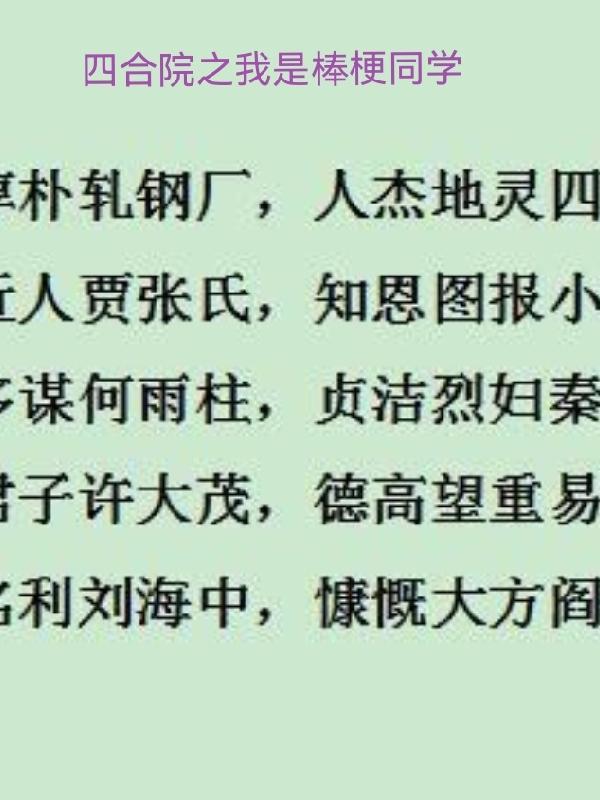69书吧>青云有路是什么生肖 > 第六十章(第1页)
第六十章(第1页)
他离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我还没有等到女帝传召。独自坐在书房里我提笔却不知该如何接着写下去这封信,霜晨直接推门而入,我笔尖的墨汁掉落晕染一片。
“栗王府被陛下亲兵封了。”
她道。
“陛下没有宣我吗?”
我收回毛笔紧盯着桌上纸张问道。
“陛下有一道旨意,殿下平定反贼重伤,需在府中修养一月,无旨不可打扰殿下养伤,”
霜晨顿了顿“这是软禁。”
不杀我,不见我,这是为何?
她大抵是因念姐妹旧情留我一命,可连见我一面都不肯,又在怕什么?
我将目光投在纸上孤零零的一个“云”
字之上,墨水脏了半字,字瞧不出字的模样,人……也没了人模样。
我挥挥手让霜晨退下,自顾自的伏在桌面手不停的捶打腰部,冬日腰痛总是难忍。又加上打斗,此刻挺直脊背都甚为困难,多年沉浮下一身伤病。
不知不觉眼皮重的很,我收回手趴在桌上昏沉沉睡去,心内想着昨日一切只是一场梦,梦醒过后一切照旧那便好了。
可……这不是梦,因为在梦里我见到了从未梦到过的人,父后。
那是一年里最明媚的正午,围猎场内马匹驰骋,我和父后坐在场外凉棚观赛。
父后望着围猎场内毫无挣扎能力的猎物忧心忡忡“若都是这般不堪一击,又怎么能在猎手里活下来。”
我眺着围猎场瞧不清场内,喃喃回答“人人都想做猎手,人人却都是猎物。”
“阿笙,从前你一直是猎手,如今成了猎物。无论是猎手还是猎物,皆要思危,思退,思变。你曾未雨绸缪思未来之危,也曾功成身退居于徽州,如今也该想一想如何变动了。”
梦里的我恍惚中思绪穿过悠悠岁月,每一个死在我手里的人都像一块巨石抛进心池之中,荡起波澜惊的狂风骤雨,这颗心何时才能落地呢?
这一困就是半月,我在王府内如同被豢养的牢中鸟,失聪失明。
屋外庭院内霜晨正慢慢扫雪,我背着手站在屋檐下望她出神,目光穿过她投向了本是最不该出现在王府的郁相亦。他站在小院门口,内搭锦衣朝服,外披着深紫貂皮大氅,冻得微红的手指上勾着一壶酒。
我身子微微一僵,缓缓抬起手来招手,望着他讪笑,再回想起那日气极同他撒气,不由得脸上燥热,言辞闪烁起来“今天天气很好。”
郁相亦深吸一口气,边走向我边无奈道“这是近半月最冷的一天。”
我侧身为他让出进书房的路,他大步迈入书房随手将酒壶置于桌面,颤巍巍弯腰探向火盆暖手“快过年了,我来替陛下送赏赐栗王府的年礼,还是同往年一般比其他王爷多四斛珍珠。”
我将手伸向桌上酒壶,拔开壶塞酒香四溢,应是陈檀佳酿,仔细闻去还混杂着一股草药香,他倒是有心了。这半月身上不舒爽,此刻作势直接讲酒灌到嘴里。
郁相亦直起身就着我的手掌一起按在酒壶之上,对我抿唇摇了摇头。我抽出手掌道“今年闵王那份年礼不用再出,陛下该再多赏我些东西。”
郁相亦嗤笑,眼里敛着宠溺之色,他悠悠提起酒壶蹲下身在碳火上热酒喃喃“陛下已经松口,只要闵王交出同阿史那勾结的朝廷官员的名单,便饶他一命。”
我心上一喜,顺势挪着碎步与他隔着火盆也蹲了下来“闵王现在在哪儿?”
他抬眸明朗一笑“已经被安置在闵王府重兵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