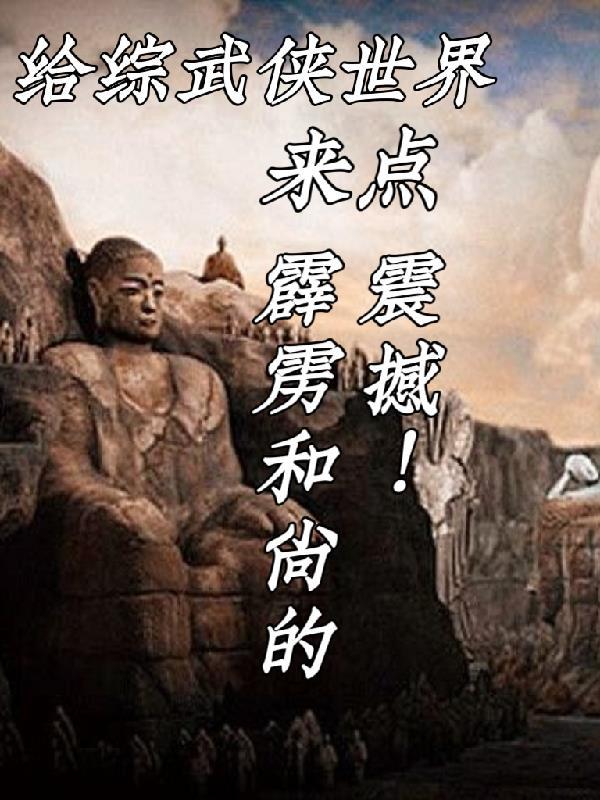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如意斋的功德利益 > 第30页(第1页)
第30页(第1页)
那杜宾还坐在罗烈边上,赤英朝徐雾使了个眼色,徐雾走过去,从背包里取出个折叠帐篷,示意众人保持距离,大家都退开,只有那杜宾还坐在原地,徐雾看着它道:“现在开始检验尸体,核对死者身份,闲杂人等建议离开。”
杜宾抬起头,眨眨眼睛,依旧没有动,黑色的帐篷支了起来,把它也包了进去。
赤英朝滕誉的棺木努了努下巴:“是今天凌晨中区警务处在这里逮捕的地球博物馆盗窃案的关联人员吗?“
滕荣点头,道:“正在举行该起案件关联人滕誉的告别仪式。”
这时候,他看了眼众人,神色沉痛,声音低沉了下来,道:“既然警务处已经来了人,有些事情,已经到了不得不和大家坦白的地步了,就在东区警务处的见证下作出说明吧。”
赤英问道:“是认罪说明吗?”
滕荣点头。
“不!”
有人喊了一声,随之而来响起了重物摔倒的声音,在这串声响的带动下,接二连三有人呼喊,摔倒的声音此起彼伏。
滕荣道:“请大家少安毋躁。”
骚动停下了,赤英颔,道:“那么您请说。”
滕荣垂下手,低着头,说道:“弟弟滕誉因为反对向地球博物馆捐赠家中油画古董等物,三天前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昨晚,东区时间凌晨一点四五十左右吧,结束了每日最后的一场聆听聚会后,大家就都回房休息了,没想到一进屋就看到了滕誉,他回来了,并且坦白告知,他把一幅捐赠给地球博物馆的油画拿了回来,”
滕荣一抬头,对着赤英道:“之所以他会说‘拿’,完全是因为滕誉对该幅画作十分痴迷,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他对它简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油画在家中保管时也是一直由他收藏于他的绘画创作室里,旁人连多看一眼都不行。可想而知,他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况都因为这幅画受到了多大的影响!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在和大家一道整理捐赠明细时才决定将这幅画也一并捐赠了,“滕荣愈愧疚,“其实原本也产生过撕毁画作的念头,但是,这样一幅画,这样的一幅杰作……”
滕荣指着滕誉的棺材,赤英拿起了棺材里的那幅油画,滕荣轻轻点头,重重叹息:“要是被毁了,未免太过可惜,这个念头就此搁置了……”
滕荣继而道:“滕誉还坦白了他拿回画作的整个过程,先,他联系上了通灵会里的旧友罗烈,罗烈正以建筑工人的身份进行地球博物馆的外墙修复工作,以工作证可以自由出入博物馆各楼层,于是滕誉便以想要参观博物馆工作楼层为借口,希望罗烈借给他相关证件,好让他可以自由出入博物馆,罗烈和滕誉关系甚笃,这里很多人也都能作证,罗烈不但向滕誉借出了工作证件,还提供了可能需要用到的指纹信息,之后,滕誉乔装打扮,利用罗烈的指纹信息和工作证,成功进入了博物馆工作人员楼层,并且没有引起任何安保方面的注意,之后,他以暴力手段破坏了鉴定科三号科室大门,取走了油画。
“接着,他继续坦白,就在刚才,罗烈找来这里,两人因为身份出借的事情生争执,罗烈质问滕誉用自己的身份做了些什么,滕誉想要辩解,罗烈硬是要拉他去和警察坦白,滕誉听到警察两个字,脑袋晕,错手杀人,他茫然了,糊涂了,他知道他做了多数人不会做的事,他也真心忏悔了,他在房中一直祈祷,一直边祈祷边等待,等到聆听聚会结束……”
滕荣充满悔恨和内疚,掉下了眼泪:“他说他十分后悔,他恳求着,祈求着,痛哭流涕,一个哥哥听到弟弟这么说,看到弟弟如此真心悔过,即便原本极力劝说他投案自,内心怎么可能不动摇呢?出于袒护弟弟的心情,出于对在世的唯一亲人的关爱,兄长掩护了弟弟,兄长被弟弟说服了,趁着夜深人静,这对在人生道路上迷失了的兄弟在花田里埋下了罗烈的尸体。”
人群中有人也低声啜泣了起来。
滕荣稍微调整了下情绪,擦拭了眼泪,接着说:“那时候滕誉还不知道罗烈已经接受了中区警务处的问询,警务处已经得知他就是地球博物馆大盗,滕誉还想着,自己以罗烈的身份进入的博物馆,盗取了画作,罗烈死了,那盗贼就死了,没有人会再追查那幅画了,他就能完全拥有它了,匆匆掩埋完尸体后,”
他哽咽着红了脸,“当时的心情实在是太过震动,连仔细掩埋尸体都做不到,只想快些了结,倘若真是有心遗弃尸体,又怎么会随便挖出个浅坑,草草埋在此处呢?
“掩埋完尸体,回到大屋后,滕誉为了平复,镇定心情,使用了通灵会里流行的一种镇定药剂,这是一种他从小就被逼迫使用,并且已经产生依赖性的药物,使用这种药物后,必须在一个极度安静的环境下待上半天,心境的平静能使药物在身体里挥恰当的镇定作用,但是中区警务处的突然出现,使得滕誉情绪激动,药物反应猛烈,导致了他的死亡。”
滕荣伸出双手:“这双手的手腕就是在试图劝说滕誉投案自时被他抓伤的。”
他道:“滕荣自愿听从正义处的处置建议。”
赤英道:“请解释聆听聚会。”
滕荣说:“每天这里都会举行三场聆听聚会,聆听自己的心声,聆听别人的心声,以便寻找和从前的自己合解的方法,清洁肉体上的污浊,召回迷失的前世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