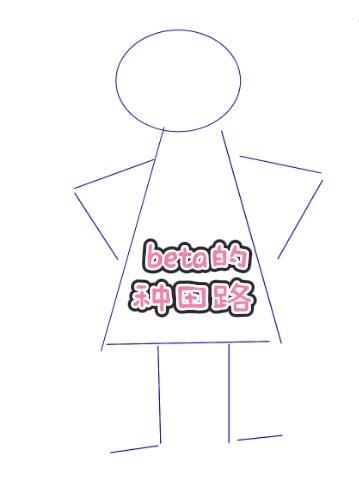69书吧>妖言惑众晋江 > 第29頁(第2页)
第29頁(第2页)
宋羽寒拿桃枝羞辱地抽他們的臉,笑眯眯地說:「不好意思,嚇到了吧?」
混混頭搖得像撥浪鼓,連聲說:「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宋羽寒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下次萬不可作惡了,知道了嗎?」
混混們:「是……是。」
周滿:「…………」
女人:「…………」
惡人要麼惡人磨,要麼拳腳磨,宋羽寒顯然是後者。
「認個錯便滾吧,下次讓我再見到你們。。。。。。」宋羽寒陰森森地笑,「我就扒了你們的褲子讓你們裸奔。」
周滿:「…………」
女人:「…………」
抽空宋羽寒回頭沖周滿一笑,眼神里寫著:看清楚了麼?
周滿:「……」
我再多長隻眼睛也看不清,他木然想到。
一時竟不知道是被打更嚇人,還是被迫裸奔更嚇人,幾人竟真的連連磕頭向女人認了錯,連爬帶滾地跑遠了。
女人神色複雜,垂眼看了一眼安靜下來的孩子,溫聲道:「。。。。。。謝謝。」
宋羽寒扔掉桃枝,靠著牆找了個台階坐下,還招呼他們也坐,等三人均坐下後,他將銀子給回女人手裡,說道:「不用謝,我們做個遊戲,全當是報答了。」
「這個遊戲叫我問你答,我問什麼,你答什麼,可以嗎?」
女人抱緊了孩子,抿了抿嘴,像她這樣的流民,拖著孩子,又無法四處流浪,最忌諱的便是嘴上不把關,禍從口出,說不定哪天就丟了小命。
可他。。。。。。。。
女人看了他一眼,安撫地輕拍著孩子,低聲答應:「可以。」
宋羽寒問道:「你從何而來?為何會落得這樣的境地?」
女人靠坐在石板階上,眼下有些烏青,她老實回答,苦澀地說:「十年前,我的父親患了癆病,我的母親受不了煎熬,自殺了,自此我與我的丈夫相依為命,可好景不長,去年官府徵兵,他去了。。。。。。從此我就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她的聲音顫抖:「鄰居見我們寡母,剛開始時還只是打打秋風,到後來便是明目張胆的搶了,他們的丈夫來敲我的門,逼迫我,我被村子裡的女人扯著頭髮按在水裡,她們朝我吐沫子,罵我是。。。。。。娼妓。」
「久而久之,我便帶著剩餘的細軟與孩子四處尋生計,可見我,實在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她小聲地訴說著自己的苦難,外面喧囂的談笑聲仿佛與她格格不入。
「……我知道了。」宋羽寒說,他深知這樣不亞於撕開曾經血肉模糊的傷口給他人看,「抱歉。」
她淚流了滿面,周滿拿出帕子遞給她,女人道了謝。
宋羽寒耳根子軟,有些不忍繼續問,但眼下事態緊急,他不得不問:「我能否問問你對茗月樓了解多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