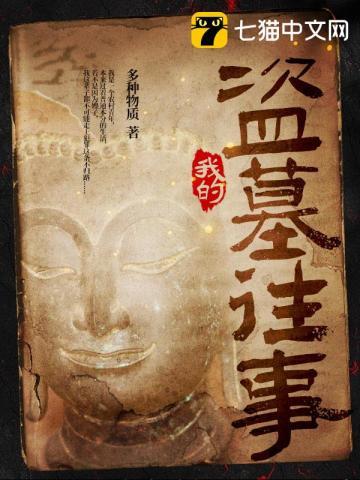69书吧>白露早 > 第12页(第1页)
第12页(第1页)
他仿佛猜到她的心思似的,主动说:&1dquo;是6柏友他们几个。本来约了晚上打牌的,结果刮台风,跟他们说改了动卧回去,牌打不成了。他们非不信我。”
她很清楚在城中想结识他的人一抓一大把,但他真正的朋友圈子就那么固定的几个人。她与他好的日子里,偶尔会陪着他与他们一起打牌。他们在牌桌上说话比较随意,有那么一两次叶至谦说漏嘴,提到他从前最爱去夜总会消遣,出手阔绰,是各路美女们争相献媚的对象。她自然能想象得到他年轻时不可能像如今这般清心寡欲,所以只是一笑置之,反而是6柏友十分刻意的狠狠睨了叶至谦一眼,还刻意把自己搭进去说事:&1dquo;我以前也最爱去夜总会,出手也阔绰。”
向来专注打牌,甚少吱声的文景松也跳出来挤兑叶至谦:&1dquo;我记得你有段时间都把夜总会当自己家了吧?”
叶至谦见形势不妙,乖乖举白旗投降。
她当时不明白为何6柏友那样急匆匆的想要将这个话题引到自己身上,后来才晓得顾子朝就是在夜总会遇到宋南妮的,也是后来才晓得她与宋南妮还是校友。
顾子朝说自己是爽了打牌的约,那便是了,他没有必要骗她,也从不会骗她。
他解释了自己为何挂断来电,又问她:&1dquo;你经常坐动卧吗?”
她说:&1dquo;想在家吃晚饭的话就会坐动卧,时间比较合适,睡一觉就到了,不耽误第二天上班。”
他问:&1dquo;应该没有绿皮火车那么吵吧?”
她想起他睡觉一直轻浅,虽然动卧是高科技产物,但毕竟是在轨道上飞运转,跟装了隔音玻璃的卧室肯定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如实的告诉他:&1dquo;只是稍微好一点点而已。”
列车驶入一条弯道,原本放置在桌板下的行李箱因为惯性滑向了他那边,撞在了他的膝盖处。
她连忙直起身子,想要把越轨的箱子拉回来。
他却先一步起身了,双手抬起箱子放到了他的上铺,然后回过身问她:&1dquo;放上面可以吗?”
她好像压根没办法说不可以,于是委婉的问:&1dquo;那他们怎么睡?”
他不答反问:&1dquo;箱子里装的什么,这么轻?”
她说:&1dquo;煲汤料之类的,不重,但很占地方。”
他蹙了蹙眉,突地笑了一下,说:&1dquo;我仿佛闻到了榴莲煲鸡的味道。”
她先是一愣,旋即也笑了笑。
他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没有喝老火汤的习惯,但饭桌上若有汤亦会喝上两口。有回家庭聚会,舒宝乐张罗着去市郊的农家乐玩,那里环境悠然自得,菜色也鲜好味,他吃了半只烧鸡,说了两次那鸡的肉质好,舒宝乐一听,临走非要塞两只宰好了的鸡给他们。他压根不会做饭,她的厨艺也只够勉强不饿死自己,思来想去,这两只鸡唯一的下场就是煲汤,既营养又省事。她问他吃不吃榴莲,他说不排斥,于是就有了榴莲煲鸡。他是拧着眉毛喝下那两碗汤的,活生生一副嫌弃又想尝试的模样。
这已是两年多前的事了,可那画面,魏霜却记得很牢,牢到随时都能在眼前重播。
她渐渐收住了嘴角的笑,心情慢慢沉了下去。她有意不去接他的话,从包里翻出洗漱用品,然后下床、打开包厢的门,往车厢连接处的洗手台走去。
她花了十五分钟的时间洗脸刷牙,又在过道里站了小半个钟。她想把此时的情形告诉谁,可翻开通信录,也不晓得能与谁说、怎么说。
十点半,她返回包厢,他不在。
她看着他刚才坐过的、此时已是空荡荡的床铺了会儿怔,然后关了灯,背对着门躺下。
韩思羽曾说,她与顾子朝分手,分的藕断丝连。到不是他们还有直接的往来,只不过她总能偶然的从各处听闻到他的近况,也时不时会有他的亲人朋友在她面前晃荡的想让她知道,他与她一样,仍是孤身,甚至连她社里的头面人物也曾透露他对她的暗中关照从未停止。
他就像她头顶那张迟迟没有落下的网,这网并不是无边无尽,也没有确定收拢的时限,他从来都是不急不缓的,甚至允许她逃,只是她自己总也迈不开脚。
是她没用。
是她常常躲在被子里流眼泪。
是她时时只能偷偷的想他。
是她放不开这段感情。
此刻,在黑暗中,她的眼泪随着飞驰的列车散落在了一路向北的轨道上。她整个人蜷缩起来,身体止不住的抖,也忍不住的出细细的呜咽声。
顾子朝是在魏霜已经哭完、情绪平复的差不多的时候回来的。
包厢里黑漆漆的,他借着走道的灯看到她纹丝未动的背影,便以为她已经睡着了。
他刚才去餐车同余一航和徐锡跃坐了会儿。
他没有提魏霜,他们也就当作压根没遇到过她。
那二人聊天南说地北,他大多时候只是听听,有时干脆连听也没听进去,光是人杵在那里。
十一点半时,一直叽叽喳喳的徐锡跃终于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他叫徐锡跃回包厢睡觉,徐锡跃连连摇头,旋即向乘务员买泡面,说自己精神好得很,只是肚子有点饿。
余一航借此请他早些回去休息,又说自己与徐锡跃下了大注,谁先睡着了谁的钱包就要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