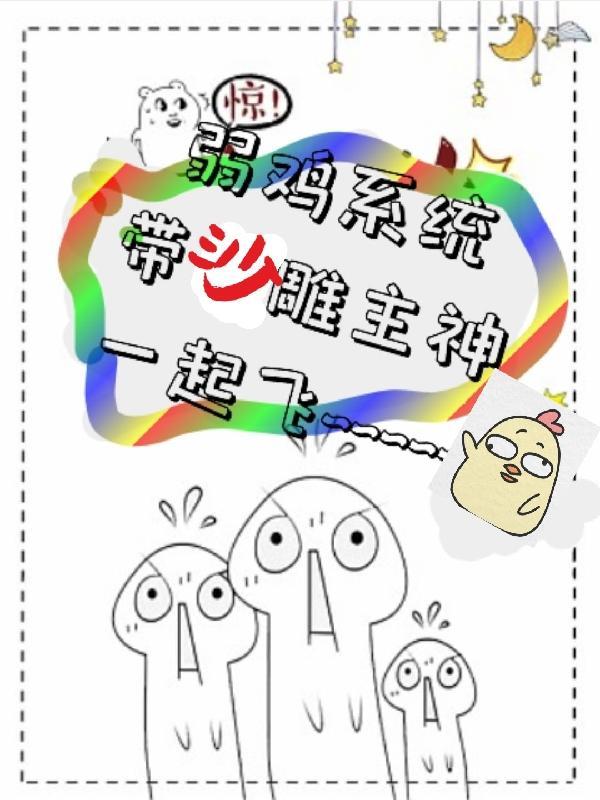69书吧>歌曲在水一方歌词歌曲 > 第69章(第2页)
第69章(第2页)
待稍有歇缓,齐戎悲叹不已,“小女心思单纯,对尚书一片痴心,怎奈她福薄,小小年纪就要…劳烦尚书陪她最后一程,也算了却她的心愿…”
齐春华去后,魏储依又在齐家留住三日。他本病未痊愈,强撑身子在齐家忙活。这日探望齐老夫人,正说着话,忽然眼前一晕,一头栽倒在地。众人手忙脚乱唤来医者,就连病中的齐老夫人也颤巍巍起身探看,口中不住念着魏尚书仁义。
齐戎念他多日辛劳,亲送他回到了魏家。
夜半魏储依断断续续起了高热,人晕晕沉沉,喉中痛痒无比,饮水都似有刀刮着喉咙。次日日上三竿方醒,他吃力爬起,但见肖燕匆匆跑来,报说福婶今晨崴伤了腿脚,已经不能行走,他得需留在家中照顾祖母,暂时无法伴行阿郎左右。
魏储依自然应允,又给他一些银钱,叫他去城中请郎中。肖燕抹干眼泪跑出门,明明坊外就有医馆,只需一刻就能到达,却足足一个时辰才回。他满头是汗,面露惊恐,“不,不好了,城中很多人都病倒了…街上有,有死人…有人说城中有大疫,眼下医馆都已关门,找不见郎中,也没有药草。南门被南边逃来的人堵着,已经无法行人,只有北门还开着,城中许多官宦百姓都逃出去了…阿郎…该怎么办?”
魏储依半晌无言,隐隐听到外头一片嘈杂,抬目望向院外,只能看见自家朱红的高门。
肖燕忙跑外头探看,一时面露大恐,“阿郎,坊里的人都要逃走,好像城门都关了!”
混乱声越来越大,邻舍也鸡飞狗跳正举家逃难。魏储依捂唇咳了声,神色还算镇定,“外头正乱着,若真有大疫,反而要远离人众。”
肖燕神色未定,听见院外喧嚣,探头哭道:“阿郎,方才我听说齐家老夫人也去了,到过齐府看诊的郎中也都染了疾…”
魏储依略略顿住,倏而面色大变,抬袖掩住自己口鼻,催肖燕离去。肖燕会意止不住哭泣,“阿郎你…这该如何是好?”
魏储依反而平静异常,叮嘱肖燕关门闭户,立即去库房拿足粮食,带福婶从门房搬到园池对岸新建的屋舍,有事无事都万万不得再过池这岸。家中粮食充足,园里蔬果也到能食用之时,一两个月应能够用。
肖燕手足无措,边哭边道:“阿郎你怎么办?十七也不在,谁来照顾你…”
魏储依说:“若齐家已染疾疫,我也不能幸免。这里不缺甚么,我可以自顾…你与福婶趁尚未病,远离正房。现在外头大乱,既出不了城,留在家里反而安稳。性命攸关,马虎不得,你只管照做就是。”
肖燕只得哭泣离去。待其走远,魏储依放下衣袖,喘息半日,慢慢挪到窗旁,望向一道碧色天空,喃喃自语,“十七…就待在上合莫要回来…”
当日午后魏储依开始浑身疼痛,车轮碾过一般,卧在床上动弹不得。
短短两日,巍峨华贵的都城换了模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外入流民,有不治而亡者就横尸路上。市集皆闭,人难购所需。不知是谁起头,米铺食肆皆遭人破门疯抢,甚有人趁夜盗入他户,烧杀抢掠,再混入流民逃之夭夭。而城中空下的屋舍,多有被人打劫占领。此时律法已荡然无存,人人自危。
城中大乱,皇宫也未见泰平,宫中诸人多有病,皇帝令众医官救治。然随疫迅扩散,染疾中除有官级者,余人尽被关到一处,有死亡或病重者,皆被拉出宫门,于荒郊焚烧尸。如此待宫中稍稳,皇帝才分心派羽林卫在城中治乱。
治乱便要立威。乱者人多势众,并不畏惧兵卫,直到一连百数暴民被当街斩杀,乱才渐渐平定。
根据御医嘱,城中所有人家皆要闭门断隔,人人不得外出,更不可串门集聚。
羽林卫驱城中民众各回各家,坊门闭阖,由坊正和卫守严加看管,终日禁制。流民则被拘禁废弃宅舍,外由重兵把守。同皇宫一般,各处死者病重者皆被运到远郊焚烧…
短日内或尚可安稳,然时日长久,百姓渐食不果腹,饿死者甚至过病死者…
西北坊位处偏僻,官居占半数以上,也大多逃离出城,只留下空荡荡的宅邸,所幸未有流民涌入,封禁后异常的安宁。是以有人悲鸣亡者时,哀恸震天,整座坊邸都罩上了沉沉死气。
魏家邻居也是官宦人家,老老少少相携逃难,只有一年迈老者因走不动路,而留下看家护院。一日,老汉向魏家投掷土石高呼救命,魏储依闻声艰难挪到门口,听其求他问粮,便用巾帕掩住口鼻,一步三歇来到灶厨,捡些米面菜蔬装入布袋,拼尽全力抛过墙头。喘息空隙见老汉磕头离去,他再难支撑,瘫软在地,足足两刻钟才有缓和。
因在外逗留时候长了,病症愈严重。最初他还能强撑倚坐,后来反复烧热,筋骨疼痛难忍,只能卧在床上。日夜昏昏沉沉,不辨今夕何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