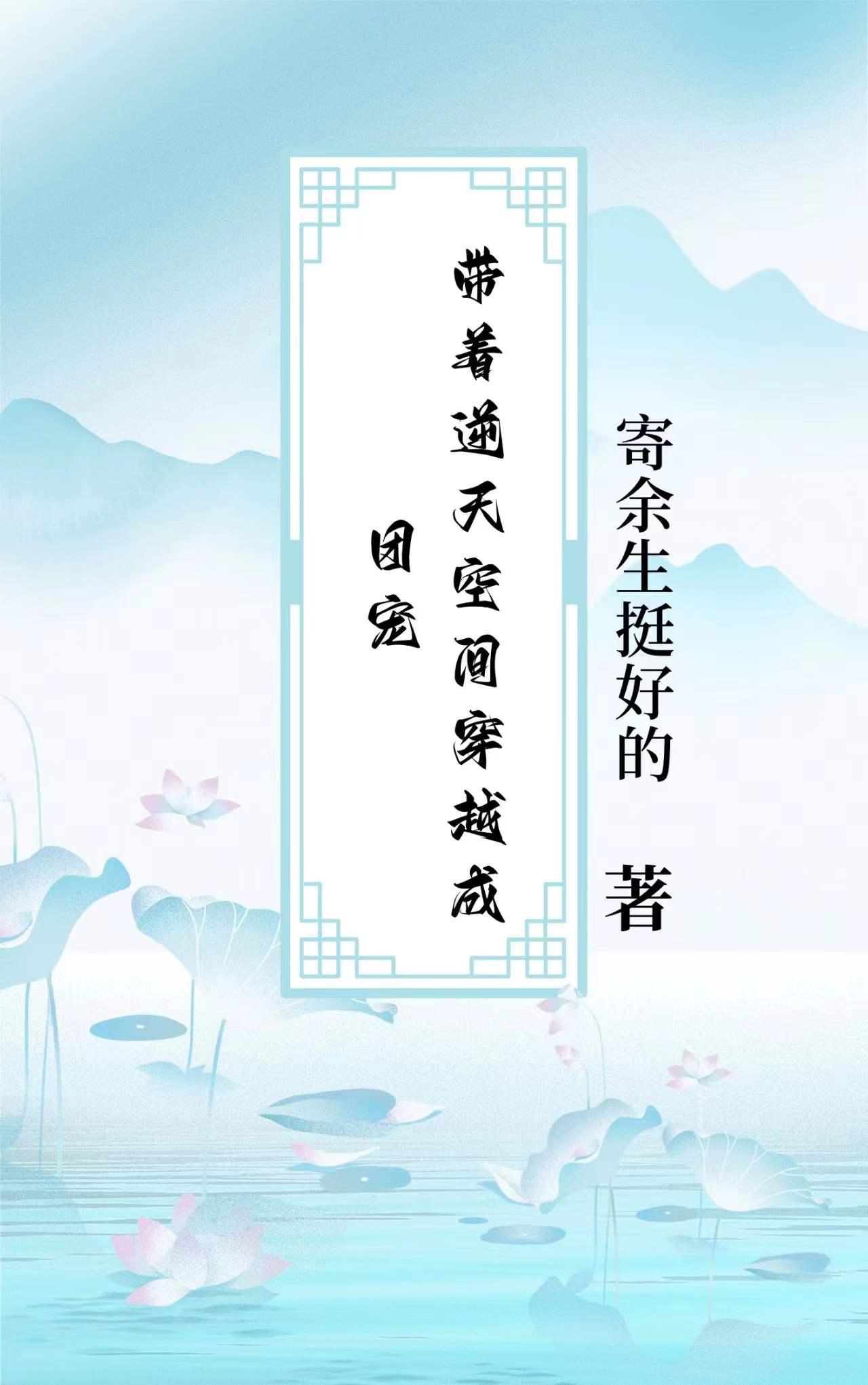69书吧>怎么老是你用英文怎么说 > 第11页(第1页)
第11页(第1页)
里头骤然一下没了声响。
这可是大事,天大的事,一不小心就要全家掉脑袋的大事。
这时夏和易前脚已经迈过门槛儿,再退回去也不是事儿了,只好装聋作哑,笑嘻嘻进门请安。见有人来,夏公爷和潘氏也就不议论了。
对于夏公爷的疑虑,夏和易是半点不焦心的,前世她还顺顺当当进了宫当了皇后,至少三年五载内夏家都没遇上什么劫难。这回许是夏公爷政见上说错了两句什么不打紧的话,叫万岁爷一时记住了罢。
她愁的是父亲归家,这对现在的她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好信儿。公爷们不被政事绊在宫里,说明眼下的政事乱局就快要散了,待太后和万岁爷挪出空闲来,下诏封后也就是眨眼的功夫。
登时便成了烫石板上的蚂蚱,来也不是去也不是。
有时候也不免感叹,人活着也不必看得太清醒,像她上辈子那样且糊涂着过,不也糊涂有糊涂的运势么。如今看人看命都太清楚,反倒处处制肘步步艰难。
夏和易迟迟坐在窗沿边上愣,风吹得叶影在青石砖上摇摇曳曳,她的心思也随着来来回回起起落落。
她为她记忆中那个安乐的夏家而难过,但托生在世家大族的人都应有觉悟和本分,生是泾国公府的人,死是泾国公府的鬼,不提家里算没算计她的前程,至少在吃穿用度上不曾苛待过她。
就冲泾国公府的前途,她也无论如何不能进宫,这辈子说什么都须由姐姐去登那皇后高位,托得夏家再往高处走一走。
既定了最远最大的想头,近的难处自然就有了答案,这戴思安看来是非嫁不可了。
一头想定了,一头又有了的难题。公府人家的亲事琐碎繁杂,即便荣康公夫人前日回去便开始不眠不休张罗,到真真过大定都且有长日子,正经过门就更不必说了,少则一年,多则好几年的都有。
可夏公爷都能够下职回府了,她实在是等不及了。
夏和易兀自坐了一会儿,下了决心,招了春翠和秋红近前来,招呼着把门一关,细了声儿问:“你们平日里在外院,可有熟识的小厮?”
事到如今,只有使银子,让公府下人在外头敞开了说,泾国公府的二姑娘,许了荣康公家的公子。
这天子脚下,说大可大,说小却也小,尤其是王公贵族的圈子,更是小之又小,不仅主子间姻亲连着姻亲,公侯府上的下人之间也是盘根错节,像这种谁家闺了谁家少爷的风月故事,男女老少都能说个响嘴儿,不几日功夫就传遍了整个京城。
心里一寸一寸灰败下去,愁眉难以周全。她拼了名声、拼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到底也算对得起夏府十几年的养育恩情了。
*
日头大盛,人影在滚烫的地板上高高耸起,耳畔蝉鸣声一茬高过一茬。
皇帝的御辇自揽胜门上过来。太后跟前最得脸的卜嬷嬷一早得了信儿,早早笑眯眯地迎出月台外,蹲身纳了个福,“万岁爷来了。”
近来天下不太平,皇帝忙得脚不沾地,好几日都是打人来仁寿宫请安。今儿政事总算处理得七七八八,好歹是能喘口气,出于孝义,头一件事便是亲自来向太后请安。
至于这里头有没有打私心算盘,大约只有皇帝自个儿能知道。
也是晨起的时候无意中记起,前世仿佛就是这一日,太后拿了两副画像让他挑选。
那宫廷画师技艺了得,不仅描出了皮相,连画中人的性子也能从画中窥见一二。
夏家两个姑娘,长幼有序,先拿到手上的是夏大姑娘的画像,徐徐展开一瞧,容貌上佳、端庄大方。
若再没旁的选择,皇帝端看画像便觉得再没挑拣,定然堪当国母之位。
可惜有两幅画像,同宗同源的二位姑娘,看了一个,不看另一个,大面儿上总说不过去。皇帝没再亲自上手,微微一颔,边儿上侍立的太监立即会意,抖开夏和易的画像,一左一右托臂展在一旁。
皇帝并不十分留心地看了一眼。
轻描淡写的一眼,只来得及扫过画中人眼底罕见的狡黠和灵动。
也就这一眼,脑中登时就冒出了画像时的画面,她定然是没心没肺地笑对画师,面上一派盎然之色。
第一反应,皇帝觉得不妥,非常不妥,简直难以置信,一向老派的泾国公夏文康,加上大学士府出身的潘氏,竟然能教导出这般不成就的女儿来。
皇帝肃寒着脸,到底没忍住多看了一眼。
脑海中的画面愈加活灵活现起来,年轻的姑娘,拧着细腰坐在一扇三交六椀的槅扇窗前,亮堂堂的日光从心屉里照进来,挽起的丝倒耀着光,将漫天星河倒影在冁然的眼波里。
深宫的日子,说是花团锦簇、富贵无边,然一日复一日的枯燥重担沉甸甸压在肩上,规矩体统讲究太过,生活只剩一潭望不见星点波澜的死水。
就那一刻,皇帝忽然思量,若是来一个与众不同的皇后同他相伴余生,是否能够装点他这一成不变的刻板生涯。
是以,他最终在姐妹俩里选中了夏二。
待帝后大婚,皇帝见了夏和易,才现她和画像上并不一致、和他的期许并不一致,她与他见过的其他大家闺秀几无差别,永远敛着眉眼,一个式样的小心谨慎、一个式样的沉默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