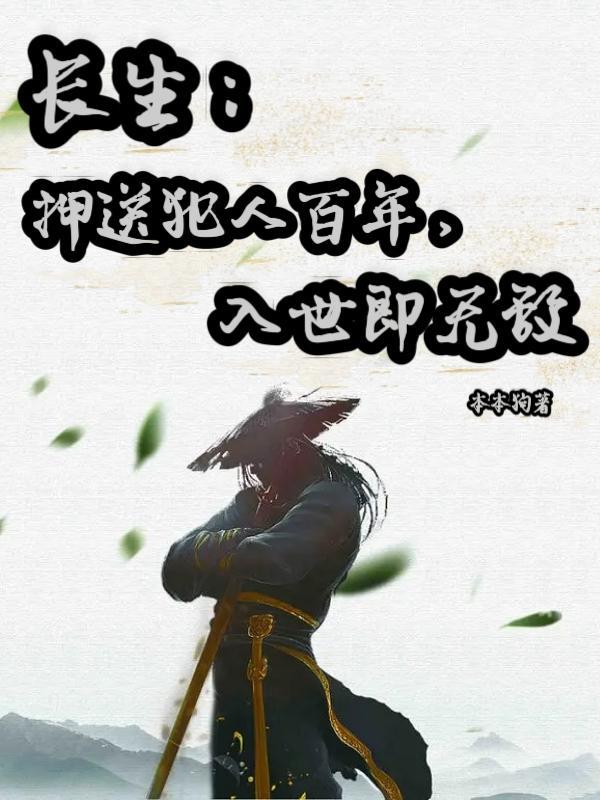69书吧>然后吃 > 第2章 矿场(第1页)
第2章 矿场(第1页)
凌恒终所处的穷乡僻壤之地名为绝涯山,虽是村,却言山,是因在村居的各个外围处都坐落着一座座长像塔似的高耸建筑物。
此屋虽与周围其他大大小小的屋子相比高不了多少,但涂抹着的白色混凝土类的石头状材料,屋顶略向外凸出,就其巧夺天空的外形而言,称得上村中最为金碧辉煌,被称为“无涯塔”
。
在村子的中央处,存有螺旋状内凹的矿场,随时可嗅到来自矿物和臭不可闻的怪奇气味。矿场一望无际,从远处来看,似有一座无底的深渊在静候着到来的猎物们。
四面八方高耸的塔将村落包围起来,联合中心的矿场,像是五指山一样把居民重重包围起来。
四处都可见不知凡几的梯子,在矿场内空气并不算稀薄,参差不齐的矿物,四面八方自愿与被迫的工人们挥洒着青春的汗水。
雨过天晴,再湿润的泥土在这炽热的阳光和人们呼吸吞咽间散的热量也得望风而降。
由东南西北西四个方向打通了的挖掘方向起,每个进入口都有一座中等大小的圆形水池,水清澈明亮,充满了吸引力,水面波光粼粼,似是诱导着人们。
湖泊中心有一座雕像,犹如正与战场奋勇杀敌的英勇战士,虎背熊腰却使人崇拜。
凌恒终与虎仇在清晨梦醒时分,便来到了矿场,无涯塔管辖着绝涯山的规矩,所有未成年都必须进入矿场内进行工作,而成年人则变为“义务工作”
,所有工资根据矿物的上供量决定。
凌恒终此时才在湖泊前看到自身的模样,那是一双清秀的眼睛,呈淡紫色,轮廓分明清晰,容貌可谓眉清目秀,谈不上帅气但也论不了难看,只能归于平凡。
从面庞左上角至约眉眼中心偏上方有一道疤痕。
‘除了这双眼睛,其余和前世相比没有丝毫变化。’凌恒终镇定地想道。
“时间快到了,我们必须赶快进去了。”
在凌恒终聚精会神观察自身时便被虎仇急迫的扰乱了思绪,每个入口处都有数不胜数的备用矿铲,时时会有人前来补充。
虽然他现在手上握着的算不上是新出炉的铲,但与虎仇手上的相比,明显更加完好,显然虎仇已经用了很久了。
前方虎仇正不断地催促着,后方矿场内地位略高一些的矿头也在愤怒地赶着人,好似世间只余下愤怒,不知何为休闲。
凌恒终跟着虎仇回到之前挖矿的地方,随着挖掘的深入,每次需要前进的路程会变得愈多起来,从有时候十余分钟便能看到目光所及之处的泥土与部分露出少许头部的矿物。
只有来自矿头们上面的人的应允下被宣告才能更换方向,他们永远是高傲的,有时即便路程极远也无法私自决定,而这种高傲也多少影响到了矿头们,不少矿头们也心生高傲或者说自大,每个区都有几十位矿头,有和蔼可亲者,也有恶言厉色之人。
凌恒终力气不是很大,每次挥舞手中的铲子都要熬心费力,或是疲倦,每次铲下一点出铛铛的声音时,便会不由自主的有一股浅睡意袭来,凌恒终很快便觉了自身情势不妙。
经过一番思索后,凌恒终终究还是将内心的迷惑压在内心,只是挥舞的动作放缓了一点,挥舞的力度也弱上一分,无论是谁从何角度观察,都只能看到忠于职守的凌恒终。
除却从那些黑心贩子里购得的些许够饱腹的食物,凌恒终可以说得上是从旦时做到黄昏。
在此地,如果不干活就没有钱,也不会有人伸出援手,甚者有不少会在一旁等候着濒死之人或痛苦或开怀地挣扎直至身亡命殒,如若确认没有孤注一掷的反扑,或许还会有人无偿搭把手,代价只是一具尸体罢了。
矿场内部冲突是被默认的,来自各处饥肠辘辘的陌生人会和过路人分享这份美食,他们或是年迈的老人或是没有能力工作忍饥挨饿的年少、残疾人。
凌恒终向来多灾多难,无论何时,麻烦总会接踵而来。人活一辈子总会有麻烦的,有时候不是在自找麻烦,便是麻烦找上门。
凌恒终和虎仇一直走在一起,两人间时而拥抱;时而搂着肩膀;时而开怀大笑。他们是兄弟,但更像是亲人。
“你先走吧,有点小事要处理。”
凌恒终缓缓停下了脚步,脸上露出行若无事的神色朗笑说着,虎仇虽然感到茫然不解,但他还是没有多想,只是默默应从。
在凌恒终漫步于逐渐远离人烟的小道上,有一道若隐若现的视线一直默默地注视着他,仿佛像是护送归家少爷的护卫珍惜着不远处的身影,防止被其他人会盯上。
他的眼神又如蟒蛇般看着自投罗网的猎物,眼神绽放出充满欲望的光芒,似狠毒,似是亢奋,似在窥间伺隙。
直至凌恒终走在只余寥寥无几,暗中的猎手便拿着一把略显锋利的银色质地小刀冲向目标。
凌恒终手握铁铲,流露出狠辣的眼神,在彼方饿虎扑食的攻势未到之时便向脑袋处猛地力连续拍打,即便显有预料到,在猎物反扑时便双手护住脑部,但长时间挨饿下的力气显然无法与常人比拟,因而很快便被击退。
这位“路人”
反应过来后,随即单手持刀准备垂死挣扎,张开像是猛兽般的血盆大口咬向凌恒终的手臂,同时咕噜咕噜的声音,宛若雷鸣般的响声不断从胃部传来。
‘看来又是一个要成为饿死鬼的人啊。’凌恒终若有所思地想到,眉头微皱,同时一手将铁铲护在身前,另一手成爪形抓向那双漆黑的眼睛。
不知名的外人显而易见没有可能性翻盘,即便眼睛被刺痛,吃痛下只能不断往后退,但依然咬到了凌恒终。
在凌恒终打算尽快帮助可怜人解脱前,那个人突然佝偻着身体,随后从嘴里吐出如流水般清澈的液体。
凌恒终警觉地打算用铁铲抗下似水的液体,但接触到的一瞬间,铁铲便被腐蚀了。
正当凌恒终绞尽脑汁思考下一步时,只见那个人眼神呆愣,身体仿佛掉线的风筝,被轻盈的风抚了抚便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凌恒终在一旁细心入微地观察了一会儿,随后缓慢靠近他,紧握手中只剩下木棍的铁铲轻轻推动了尸体,凌恒终见那个没有任何反应后才如释负重松懈了下来。
正准备处理这全身苍白的尸体时,却瞧见尸体不断萎缩,慢慢蜕变成一颗圆形的球,直到缩小到手拇指般的大小。
在凌恒终没有来得及反应之时,球状物品风驰电掣般的飞向了凌恒终。
‘亏大了。’
在凌恒终直愣愣倒下来前,这是唯一的一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