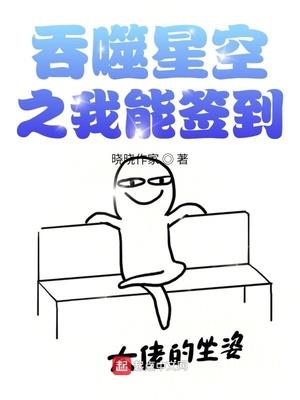69书吧>他们是冠军英语怎么说 > 第3章 我宁愿被人讨厌(第1页)
第3章 我宁愿被人讨厌(第1页)
我宁愿被人讨厌,也不愿被人可怜。——迭戈·马拉多纳
龙峤跳起来,朝前迈出又顿住。
脚一伸,把那张滑走的塑料凳勾回来。脑子还在迟缓转动,香烟已经收起,左手熟练拽下巨星同款的飞行夹克,吧唧朝凳子上一罩。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完了才暗骂傻逼。
谁要坐?坐个屁!没见这夹克都他妈脏成啥样了?!
同他这个人一样脏。
在血和土里滚得久了,污秽早就渗透皮肤,刻入骨骼,烂泥一样裹着他,教他迈不动腿,直不起腰,张不开嘴,只剩双眼睛看得目不转睛又惊疑不定。
“你……你怎么在这里?”
怎么在这座小县城?
怎么会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沾着泥污的板鞋?
怎么会任由衬衫松松垮垮套在身上?挽起的袖子下双腕素白,没有任何装饰。丝缭乱,被汗水黏在耳边,本该皎如明月的脸晒得绯红。整个人看上去又热又疲倦,像一朵牵牛花蔫耷耷开在午后。
这是方蔚然,又不似方蔚然。
好几个可怕的猜想同时闪过。
但当眼前人仰起脸,笑微微看过来时,他又分明看见了光。
“抱歉,刚才没听清。请问吴顺在哪里?”
温婉恬静,带着对陌生人应有的礼貌和矜持。
龙峤愣了愣,一脚把凳子踹到身后,下意识抬手搓了把鼻子。
鼻梁骨隐隐作痛。这里断过不止一次,有几次复位不够准确,也没有多余的钱去做整形,所有轻微的变形积攒起来,就形成现在这个狰狞的弧度。
左边眉毛也缺了块,棕红色的伤疤一直覆盖到太阳穴。他在上面纹了一只蜘蛛,希望能得到“萨巴隋俄”
的庇护,远离疾病和伤痛。也不知是刺青师手艺不行,还是他的西班牙语不行,侗族传说里带来吉祥的蜘蛛神被纹成了克系怪兽,实在罪过。
说不定正是这个原因,他脸上、身上叠加的伤痕一直没有断过。
最惨烈的一道伤让他的喉软骨骨折脱位,声带永久受损,只能像野兽一样低哑嘶吼。月光下弹着牛腿琴给心爱的姑娘唱歌什么的,做梦去吧。
十年时间,足够把他们都改造成陌生人。
这样挺好,真的。
“找吴顺……开网约车的那个吴顺?”
他垂下眼,粗声粗气地问,带了丝不易觉察的焦虑,“你是他谁啊?”
“是这个吴顺没错。”
方蔚然微笑颔,忽略了他真正关心的那个问题。
龙峤喉结滚动,还想追问,门外噔噔噔跑进来一个人。
吴顺手挥一堆检查单,咋咋呼呼:“哥你咋子还没缝针哩?大夫讲天气热要化脓的——”
抬头撞见方蔚然,这小子脚底一刹,赶紧扶着门框站正:“方、方书记?你咋子会在这里?”
方蔚然朝他笑笑:“你认识我?”
“州上来的美女领导,啷个能不认识?”
吴顺笑得殷勤,还有点儿小得意,“你每天早上不是会去小学门口吃卷粉嘛?那个摊子就是我阿婆摆的!”
方蔚然的笑就真实了许多:“你就是吴阿婆家的吴顺?”
两人的交谈龙峤听得分明,左眉上那只蜘蛛不由自主扭动起来。
方蔚然现在是个“领导”
,这让他松了口气。
很多年前他就知道,她会走上同她父母一样的道路,要么高校,要么体制。有些人天生就应该住在象牙塔和水晶宫里,永远清澈明亮,不沾丁点儿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