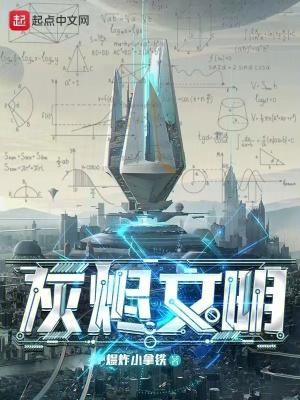69书吧>嫣然天使基金 > 第七十四章(第3页)
第七十四章(第3页)
顿时那眼泪再忍不住,啪哒一颗落在周鸿手背上,扭头钻进了车厢里。
周鸿只觉得手背上被烫了一下一般,本是想骑马的,这会也顾不得了,跟着就进了马车,挤得丹青只好坐到了车辕上。车夫轻轻晃了晃鞭子,马车便慢慢动起来,驶出了晋王府的大门,直往家里走去。
顾嫣然在车厢里哭得不成样子:“你,你总算回来了,有没有受伤?吃了不少苦吧?”
周鸿被她哭得手忙脚乱。他一出宫回了家,就听说妻子来了晋王府,于是衣裳都没换就跑来了,只是这会儿见了人,反倒不知该怎么办了,只能反反复复地道:“我没事,你别哭,我真的没事。”
顾嫣然足足熬了有四个月,这会儿一哭起来自己也没法收场,足足哭到马车到家,这才勉强停下来,自己觉得有些丢人,哑着嗓子支使丹青:“去拿顶帷帽来。”
哭成这样进门,被人看见了还不知要说什么闲话。
帷帽取来戴好,周鸿小心翼翼牵了她下马车,回了小山居忙叫人打凉水来给她净面。夫妻两个折腾了半晌才能相对坐下。顾嫣然红着眼睛看他:“当真没事?”
“当真没事!”
周鸿恐她不信,特地站起来伸伸手踢踢腿,“只不过受了几处皮肉伤,如今都好得差不多了。”
“这还叫没事?”
顾嫣然的眼泪又要下来了。周鸿连忙上前搂了她,温声道:“当真就是皮肉伤,丝毫不碍的。倒是你,眼瞧着就瘦了许多。我也料到你必然担忧,只是当时6镇笑里藏刀,舅舅来得急,机会又是稍纵即逝,委实来不及派人回来送信……”
“舅舅?”
顾嫣然忙收了眼泪,“是听说舅舅跟你回来了,人呢?”
按说齐氏是妾,齐大爷也是不能叫舅舅的,只是既然周鸿都这样叫了,她难道还会作对不成?
周鸿深深叹了口气:“舅舅在羯奴那里,当真是够隐忍!他如今在宫里呢,当初西北重关那场仗,颇有些蹊跷之处,只有他知道。”
西北重关战役,纵然顾嫣然这样不出闺阁的女儿家也知道。因为那场战役里,把守重关的老平南侯父子双双战死,而百里之外的老潞国公救援却姗姗来迟,导致重关一度失守。因为这个,平南侯府与潞国公府曾经还交恶过,直到如今的平南侯夫人嫁进门,才渐渐修复了两府之间的关系。
当时,齐氏父子任军中参赞,也在重关,正是老平南侯麾下。平南侯世子并非在重关失守一役中阵亡,早在羯奴大举进攻重关之前,他便在一场战斗中身中流矢而亡。老平南侯痛失爱子固然伤心欲绝,然而他是重关将领,并不能离开,便托齐大爷将儿子的尸身送回后方,以便送回京城。
棺木要出重关,少不得要开城门。然而城门一开,便有一支早已埋伏好的羯奴骑兵冲出来,因守军不忍叫平南侯世子的棺木落在城外,关门慢了些,被羯奴骑兵冲了进关。此刻羯奴也是大兵压城,里应外合,破了重关。
“舅舅受伤,被一群百姓带着逃出了城,却遇到一股羯奴人,都做了俘虏。舅舅苦熬了几年,因为能书能文,被一个羯奴将领要了去,才渐渐的能接触些羯奴的军情。”
周鸿神色冰冷,“当初老平南侯派人去潞国公处求援的几队人马,都被人杀死了,潞国公根本没收到求援,还是他派出的斥侯觉不对,回去报了信,才领兵来救的。只可惜晚了。”
顾嫣然听得心惊肉跳:“那些埋伏在城门外的羯奴人——”
“是。”
周鸿轻轻点了点头,“有内奸。就是平南侯世子中的流矢,也是在肩背上。舅舅疑心,那箭是从我们自己人战阵里射出来的。只可惜舅舅是国朝人,并不得羯奴人的信任,他努力了这十几年,也没能打听出来这个内奸是什么人。不过他却绘出了羯奴的地图,又熟谙羯奴人势力的分布。去年那一场仗打得羯奴四分五裂,舅舅现了机会,便带了地图逃出来。他身子不行,多亏认识了一名新俘虏,年纪轻身子壮,硬是背着他逃到边关,我们这才得见。正因有了舅舅这张地图,我才敢率兵出击,直捣羯奴内部!”
“那舅舅呢?如今还在宫里?”
顾嫣然想起齐家似乎也有个投敌嫌疑,不由得有些担心。
“舅舅有皇上安排呢。”
周鸿拍了拍她的手,“明日舅舅要上朝献羯奴地图,我也要去献俘。我想——这下舅舅就能洗刷齐家的嫌疑,不过他身子只怕熬坏了,我想——日后替他置处宅子,孝顺他两年。”
如今他过继到了长房,跟齐家更没关系了,虽然想把齐大爷接到家里来养着,却也不成。
“好。”
顾嫣然立刻点头,“我这就去寻处合适的房子。还有那个背着舅舅逃到边关的人,也该好好谢谢他。”
周鸿笑道:“那人年轻,刚去边关当兵就被俘虏了,如今只想还回去当兵立军功呢。我瞧着,这次等向皇上回完了此事,再替他安排。听说他家乡是福建的,倒是跟你算是同乡呢。”
顾嫣然微微一怔:“是么?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吕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