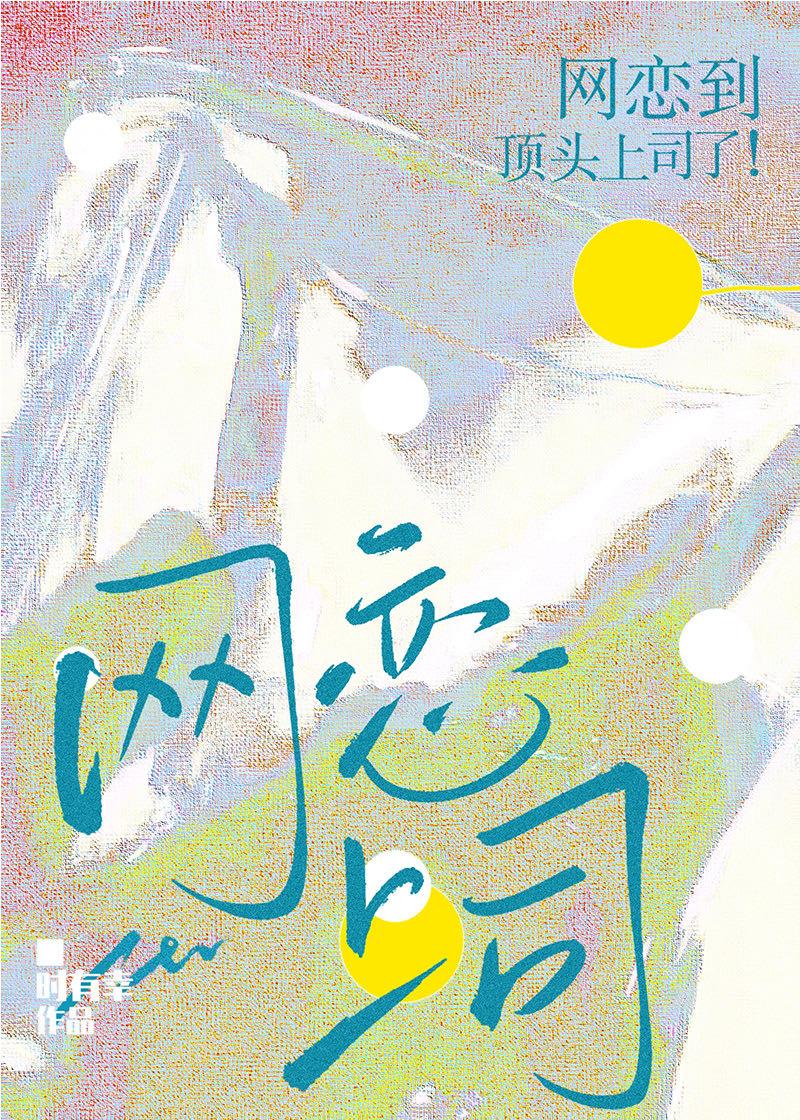69书吧>妖妃是谁 > 第67页(第1页)
第67页(第1页)
靳言娇俏一笑,“那可是龙椅,我不敢。”
“那我重替你备上一把座椅,届时可不能再倔了。”
闻言,靳遥满目震惊,这兴隆帝是准备让自己时常跟着他去上朝?
“阿遥,你从御座之下立于龙椅之侧,皆是朝堂。”
兴隆帝环抱靳遥,“所以,你不必惋惜。”
原来,兴隆帝在靳遥沉思之时便看到了她的落寞,可错已造就,他只恨自己难以挽回。
靳遥拥住兴隆帝腰腹的手臂轻轻一颤,“好,皆是朝堂。”
嘴上如此应答,心里却依旧坚定。她满怀恨意,连自己都不可以谅解,更遑论其他人。都是朝堂,但却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隐私肮脏,她不可以不在乎的。
兴隆帝轻掩双眸,不敢去看靳遥的眼,心知肚明的二人不过是在掩耳盗铃罢了。
……
夜半时分,天色阴沉,浓雾突降带着难耐的寒凉。
宁安王府破落的院子里,苏老漏夜而至。
昏黄的灯笼被夜风吹得摇摇欲坠,宁安王此刻正在堂中清点家当。陈婉应了与他的婚事,怎么着也该着手准备了。陈家本家是在楚都,成婚必是要在此地的,想来他这都城的府邸也该翻翻才是。
房门被叩响,苏老单薄的身形嵌在半敞的门框里,更显瘦弱。
“老?”
宁安王起身上前迎去。
“今日之事,谢过王爷了。”
苏老还未踏入房门便朝着宁安王弯下了身恭敬地行了礼。
在朝堂苏老本欲死谏之时,宁安王拍着他的肩头也不过就说了句,“老。您当知道,这错归根究底是在陛下的,自古名臣,哪有与一个女人论是非的。”
宁安王随意摆了摆手,扶着苏老到堂中坐下。
“只此一事怕不值得苏老来这一趟吧?”
苏老抚着胸口轻咳了两声,日渐浑浊的眼中有了些湿润,“主君如此,江山何寄?”
苏老也是明白的,他自不愿将一切归咎于靳遥。但他是臣子,怎敢不敬君主?他只能尽规劝之责。
到了如今这地步,若是有人能让君主醒悟,或是能替君主分担一些骂名,重拾一些名声也是好的。他自私地这样想着。
所以他任由赵兴去构陷靳遥,将许多污水泼洒在她的身上。他腆着老脸并未阻止,甚至在身后推波助澜。以至于今日宁安王一席话才能轻易刺痛他的心。
“大楚早现颓势,您老如何力挽狂澜?”
宁安王的话也毫不客气,“您可别想着我会帮您,本王是巴不得这楚家的江山赶紧败了。”
苏老想要反驳,却在抬眼望向宁安王与先王有几分相似的面容时顿住了。皇家与宁安王的纠缠,到底也是先帝昧了良心。
“老臣知晓了。今夜前来,倒是唐突。宁安王保重,告辞。”
他拱手行礼,脚步带风地迅离开。
宁安王满不在意地继续倒腾着那些个金银锭子,全似苏老未曾来过一般。
第39章密信风波
自从那日大朝会后,兴隆帝格外的黏靳遥。三日来竟是赖着连常曦殿也没踏出一步,靳遥有心召靳言询问长明渠一事却不得空闲。
今日清晨,靳遥板着脸将兴隆帝撵走自己去了御书房,这才有机会让金钊去寻了人来。
靳言身为工部尚书,寻常本不必日日守在临江县,但他为了显示自己对靳遥的忠心事事亲力亲为,这也有好几月未曾回过楚都了。
两人照例寒暄一番,靳遥见没什么异常之事便想让靳言见一见靳涵,她正想开口,靳言却慌张地跪地向靳遥告了罪。
前些日子,长明湖的拓宽已尽尾声,长明渠那渠道再挖上小半年便只等着将其与长河贯通,这工程也就结束了。
身为工部尚书自当未雨绸缪,靳言想了许多法子,都不能便捷地将长明渠与长河贯通。开凿缺口必然只能用人力,届时长河之上河水倾泻而来,那些开凿的人哪还有活路?
他靳言虽不是什么良善之人,但也不愿妄自背负众多无辜人命。
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炮仗作坊的年轻东家替他递上了一个法子。那人说他经年专研炮仗制法,早年曾出了次差错,以至于炮仗的威力大了数十倍,直将他的作坊都炸毁了,还伤了好些人。
那作坊东家将错失的配方记录了下来,以确保自己不会再犯错。当他在酒宴之上听得靳言的困恼突然有了这想将它用于开渠的想法。
当时靳遥无法联系,靳言只得自作主张将那作坊老板收在自己麾下,甚至给了他一小小官位,让他全权料理此事。
大楚开国至今,从未有过贫民入仕的先例。这世家皇族间的等级制度是相当严苛的,百年前曾有贫民意图蒙混其中,最后却被处以了极刑。
靳言大着胆子做出这事也是猜想靳遥不会因此怪罪,若问他为何这样觉得,也不过是因为他信服靳遥,总觉得她不会是那等墨守成规的人。
正如靳言所想,靳遥的确毫不在意这些,她所要做的正不知如何开始,这人的出现未必不是助力。
“二叔先起身来,这事你细说与我听一听。”
靳遥弯腰扶起靳言,面上喜怒不显。
靳言先是抬了头,而后惊觉冒犯又快垂下,继而站起身,“是,谢娘娘。”
“那人名叫王响……”
靳言躬身垂立,埋着头将自己的惜才之心狠狠剖析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