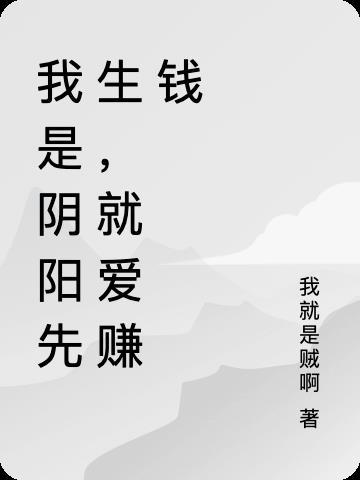69书吧>针尖蜜番外关于江海树的二三事 > 第4页(第1页)
第4页(第1页)
“卫医生吗?嘿,他哪会缺女朋友?我爸前一阵散步还看到他从家里送个女孩子出来。我也见过他把女人带回家过夜,也就是前几年的事,两人半夜偷偷摸摸地出来买宵夜,搂得紧紧的,那女的是个瘸子,跟我爸看到的绝不是同一个人!”
隔壁帮父母卖烧卤的小方见他们聊得起劲,也加入了八卦的行列。他打小住在金光巷,也年轻,看人待事的角度又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街坊不一样:“不想结婚罢了,你们真以为他活的像个菩萨?他刚搬到这儿的时候也是和女孩子住在一起的,听说经常换人,全是漂亮的小妞。”
“你和你爸眼神都不好!”
莫阿姨很不高兴自己认识的那个五好青年被小方描述成风流浪子。可她忽然想起了刚才在楼道口遇见的那个带着墨镜的年轻女人,太扎眼了……她眼神好,当时却没好意思细看。等她意识到那女人是去二楼卫嘉家的时候,只来得及将对方的背影瞧了个仔细。高个子,白皮肤,虽说瘦得很,但长腿细腰,走起路来比跳舞还好看,匆匆一瞥也不像是好好过日子的。看来这男人呐,无论老幼好坏,都喜欢长得漂亮的。
“你们说的那个小卫医生是在哪里开诊所,专治什么的?我这一阵总是头晕,不知道他能不能帮我看看。”
小方对卫嘉感情秘辛的描述,为不那么熟悉他的人填补了小卫医生形象的另一面。前头牛肉摊主的年轻老婆动了心思,眉目含春地问大伙儿。
莫阿姨早就看不惯她那副模样,每有长得端正些的男人过来买牛肉,她恨不得把自己那身肉也贴上去。莫阿姨心里“呸”
了一声,说:“他那诊所就在巷子口,你别走错了。”
“那我明天就去。”
牛肉西施雀跃道。
她话音刚落,周遭的人都笑了起来。小方和莫阿姨笑得最是大声。老吴好心,清清嗓子提醒道:“小卫医生呐,他是个兽医!”
卫嘉上了二楼,家门口并没有人。今天的来客知道备用钥匙放在何处,因此他也不吃惊,默默开门进去。玄关处添了一双女鞋,客厅空荡荡的,但尤清芬的房间开着门,灯也亮了。卫嘉换了鞋径直往厨房走,嘴里招呼着房间里的人:“不好意思啊,我下班晚了。你先坐一会,很快就开饭了。”
没有人回答他,大约是在忙着。都是熟人,卫嘉不以为意,一心只想赶快把饭做了。洗菜时,龙头的水从绿油油的菜叶和他手指尖流淌而过,他试图忽略心中某种从进门时就开始存在的异样感觉——哪里都没问题,可就是不对劲。
严格说起来,这种让他如芒在背的感觉应该在莫阿姨描述他今晚的客人长得如何如何时就开始酝酿了,或者更早。他眼前没来由地闪过回家路上瞧见的一辆绿蚱蜢似的跑车,还有门口那双看上去不便宜的尖头女鞋。饶是他对女鞋没什么研究,可那样式、那鞋码、那不规整的摆放位置……一股激灵的寒意从脊椎直窜到后颈,他未被水沾湿的手臂上,汗毛悄悄立了起来。
这种生物对于危险逼近时的本能预判驱使着卫嘉关上水龙头往尤清芬的房间走去,短短十几步的距离,他心中反复回荡着两种声音:不会吧,见鬼了!不会吧,要命!
见鬼……要命!
这声音最后定格了。
他看到尤清芬一如既往地斜靠在床上,面色冷淡黯黄。她床边用来放药的小矮桌旁围坐着两个人,那个正在摆弄墨镜的身影察觉到他的靠近,回头嫣然一笑:“饭做好了?”
卫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因应激产生大量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导致心肌收缩力增强、呼吸急促。这个房间采光不是很好,尤清芬也不喜光,平时都是昏暗沉寂的,还有一股药味和病人长期卧床的体味。现在顶上明晃晃的光源和那人身上肆无忌惮扑过来的香水味让卫嘉又添了几分眩晕。
陈樨没有理会卫嘉表现出来沉默和冷硬:“我以为你第一句话会问我回来干什么?”
“与我无关,你赶紧走。”
“原来你下厨不是要欢迎我?我有点失望。”
卫嘉无意与她浪费口舌,寒着脸问:“你怎么进来的?”
他不认为尤清芬能爬出去给她开门——要是尤清芬知道来的是陈樨,怕是恨不得在门口顶张桌子。
“这要换我问你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也不换锁,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吗?”
陈樨语重心长道。
她就是卫嘉这一生遇到的最大危险!离开时她明明把钥匙交了出来,什么时候留了一把?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的目光被矮桌上的玻璃杯锁定,杯里有黄色的透明液体。
“那是什么?”
他深呼吸,指着杯子问。
“餐前酒啊!”
陈樨答得顺畅,“口感还不错,你要不要来一杯?”
“你哪来的酒?”
近年来卫嘉滴酒不沾,尤清芬是个病人,所以这房子里不可能有酒出现。
“厨房里找到的。”
陈樨晃了晃酒杯,姿态优雅地抿了一口。
卫嘉想起来了,那不是他用来做菜的料酒吗?他嘴角抽搐:“你倒是不挑剔。”
“我挑不挑剔,你不是早就知道了?”
那瓶料酒卫嘉平时用得不多,他记得还剩下大半瓶。他在矮桌底下找到了它,不出意外地只剩个空瓶。陈樨两颊有可疑的红晕,说话间媚眼轻狂,可见喝了不少。桌上的三个杯子,只有她面前的那杯见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