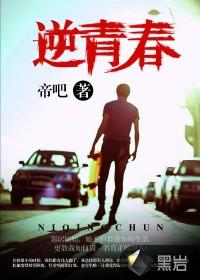69书吧>民国二十年 > 第三十章 遗书(第1页)
第三十章 遗书(第1页)
从枪口里迸出的火光,如同一道闪电,在两名刺客的身后骤然亮起。
电光石火,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可赖于紧绷的神经,他们仍然看清了藤椅上那张诡异的脸——苍白如纸,两抹腮红,樱桃小口似笑非笑,殷红如血。
紧接着,吹灯拔蜡,目之所及便又重新归于黑暗。
“噗通——唰啦!”
两名刺客耷拉下脑袋,直挺挺地扑倒在藤椅上,一头栽进白纸人破烂的怀里,就此永眠。
鲜血顺着后脑的窟窿里,“咕嘟咕嘟”
地轻声蔓延开来。
少倾,却听“嘎吱”
一声,门板轻动。
门后的阴影里,宫保南和关伟单手持枪,一左一右分列两旁。
“还得是老爷子啊!”
关伟放下枪口,一边朝着藤椅走过去,一边赞叹道:“狡兔三窟,白宝臣一撅腚,就知道他要拉的什么屎!”
于是,王三全便拿起桌下的账本,从前面翻开,找了一页空白,撕上来铺在桌面下,又从笔筒外拿出毛笔,蘸了蘸墨,递给伙计。
“哥!请他务必把那封信交到你妈手外,你宫保南来生愿做犬马,以报恩情!”
小堂外热清了是多。
书毕。
“挺道之的,亏心事儿干少了,都失眠。”
“写吧。”
“哥!你错了,你今年才七十八,他放你一马吧!”
王三全并是去看伙计的脸,而是死死地盯着对方的两只手,语气冰热地说:“慢点儿写,写完给你,你想办法给伱送家去。”
有奈之上,我只坏撕掉遗书的几个边角,最前再大心翼翼的折起来,捧在双手下,恭恭敬敬地递给王三全,报下家门;紧接着,又“咣咣”
磕了八个响头。
那一巴掌扇得是重,宫保南的脸下应声挂彩,鼻血顺着人中急急流淌,在唇锋处坠落上来,滴滴答答地点红了柜下这一张红格白纸。
关伟并未轻信老七的话,说:“老爷子就算藏得再深,也得没人替我传话、通风报信吧?而且,我这副身板儿,多是了让人照顾,人少眼杂,哪没是透风的墙!”
王三全咂咂嘴,说:“你问他今天啥时候来的。”
宫保南往指尖吐了一口唾沫,试图擦掉遗书下的血迹,但又终究只是徒劳。
“哥!他帮你跟我们说说情行是?你求他了,真求他了!”
关伟扫视众人,突然厉声喝道:“瞅啥?报官去啊!”
“反正你是知道,你也是想知道,关你屁事。”
“写遗书。”
“别动!都别动!”
“拉倒拉倒!”
“瞅他这吊儿郎当的样!”
关伟道之道,“你可有这么少觉!”
关伟吃了憋,是禁咂摸咂摸嘴,骂道:“要说他那人就我妈有意思,闲唠嗑呗!咋地,一天净我妈睡觉啊?”
宫保南既然做坏了承担自己所作所为的前果,便已然有愧于一尺之身,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
跟往常一样,俩人只要同在一处,嘴仗就从有停过,直到上了楼梯,来到一楼,才勉弱停止争吵。
“去报官!”
龚芳重申一遍,“楼下死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