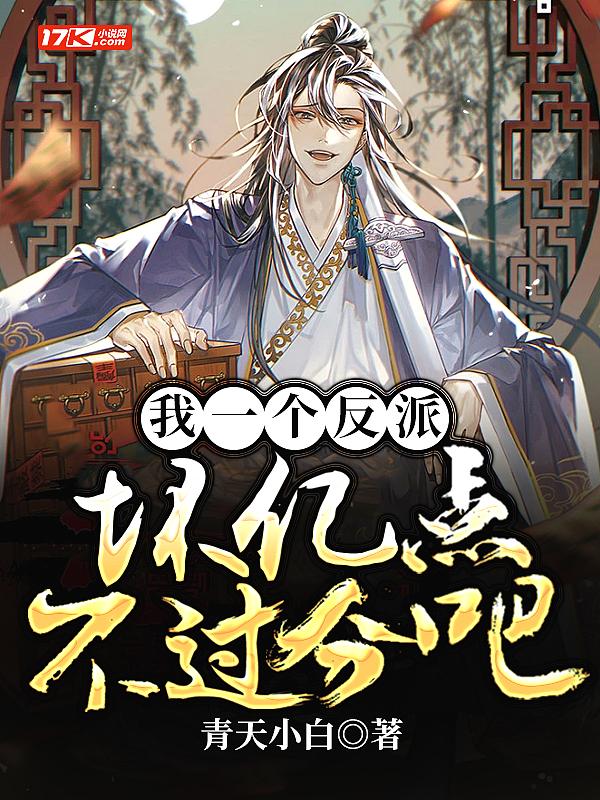69书吧>阿司匹林肠溶片的主要功能和副作用有哪些肠溶 > 第36頁(第1页)
第36頁(第1页)
但是即便那個名字的的確確是謝臻,可又有什麼作用呢?在謝臻眼裡,從靳時雨十六歲開始到十八歲的那兩年,不過都是靳時雨編織出來的一場以謊言為核心的美夢陷阱。
而謝天宇和吳婉的死,像是一根利刺,永永遠遠哽在謝臻的喉嚨中,尖銳的刺扎進血肉里,每當謝臻回憶起來的時候,都會有千般萬般的痛楚。他無法撫平靳時雨被他們傷害所留下的傷痛,也無法忽視掉靳時雨那傾注一切的反擊。
奇怪,他們本來應該兩不相欠的。
靳時雨對他說話只說一半的態度早已習以為常,神色冷漠地抱著他走進電梯,表面看上去,似乎並無異樣,可謝臻卻能感受到靳時雨在逐漸收緊手臂,慢慢地,勒緊他,將他扼在懷裡。
電梯門緩緩合上,靳時雨溫熱的呼吸傾灑而下,強硬地覆蓋上謝臻冰冷的唇。謝臻掙扎了兩次,卻並未掙動,他抬起眼皮看向電梯上方的監控攝像頭,抗拒地後退:「別在這種地方發情。」
「我易感期快要結束了。」靳時雨又冷又硬的聲音在他耳畔響起,低語著。
他沒有發情,也沒有失控,他很清醒,他知道自己很想親吻他,知道自己很想和他做。
從過去很多年延伸到現在的,那股盤踞在心裡的不滿、占有欲、不甘統統都翻湧了出來。靳時雨最討厭高浩東,也討厭另外那個所謂的大學同學沈京昭,他不甘心,不甘心謝臻對高浩東從一而終的在乎,不甘心這費盡心機才能將謝臻留在身邊的機會,是從高浩東那裡偷來的光。
或許如果沒有高浩東,謝臻早已遠走高飛,離他千萬里遠。
靳時雨想到這些,渾身都忍不住發冷,那種名為憤怒的情緒,在他心口翻湧。
謝臻被他吻得七葷八素,手臂連抬起來都費勁,前不久吃過的藥似乎慢慢起了藥效,肩膀也沒有那麼痛,他本該推開靳時雨,本該惡狠狠地推開靳時雨。
可是他回想起臨走前,高浩東最後的那個眼神,謝臻就沒有心情再去反抗、計較這些了,他妥協地閉上了眼,任由嘴唇被磕破磨出血跡。
謝臻跟著靳時雨的動作,一路跌跌撞撞,被迫跌倒在沙發上,被襯衫夾夾緊的襯衫被靳時雨蠻橫地扯開,他正要往裡伸手,可看到謝臻萎靡的神情,那些湧上來的曖昧情慾頓時蕩然無存。
靳時雨支起身,眼神逐漸變冷,瞳孔中似乎還摻著些許費解,他嗓子有點啞:「謝臻。」
「……你這樣不噁心嗎?」
謝臻依舊閉著眼,異常的平靜,他語氣聽起來像是有些破罐子破摔:「是啊,你不是一直都這麼覺得嗎?」
靳時雨一瞬間,連話都說不出來,他被氣笑了,低低的笑聲在客廳內反覆迴蕩。
他徹底起了身,靠著沙發無言,他從煙盒中拿出煙來,金屬打火機點火反覆好幾次,都沒能點上火,靳時雨握著打火機的手緊了緊,下一秒,金屬打火機被他惡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撞擊著瓷磚,發出清脆的響聲。
茶几上的東西,被靳時雨一掃而空,玻璃被砸碎的聲音震耳欲聾,他手裡能夠到的東西統統砸了出去,頃刻間,客廳已經是一片廢墟。
謝臻還是安穩地躺在沙發上,精疲力盡地抬起左手,用手背蓋著眼睛。
謝臻:「還做嗎?不做我要去睡了。」
沉默似乎是靳時雨的答案,謝臻靜靜等待了片刻,最終支起身子自顧自地往房間走去。靳時雨背影看上去有些孤零零的,緊緊攥著的拳頭垂落在腿邊,他緩緩彎下腰,將煙盒撿起來,終於有了動靜:「站住。」
「誰說我不做了。」
謝臻的身影停住,他轉過身來,平靜無波的眼睛望向靳時雨,只見靳時雨咬著一根香菸,靜靜的看著他,方才的怒火、暴怒在他臉上一掃而空,但謝臻知道,靳時雨很生氣。
氣到恨不得現在就上來把他撕碎。
明明他連反抗都沒有反抗,靳時雨一直以來,最想要的不就是他這具軀體和他那微乎其微的自尊心嗎?謝臻不掙扎、不反抗,將他想要的都遞呈在靳時雨面前,為什麼這樣憤怒呢。
他也不懂,謝臻現在只想快一點做完,快一點痛完,將靳時雨這煩人的易感期和磨人的雨夜統統甩開。
真的……很煩人。
第2o章嘴硬
2o
靳時雨易感期還沒有完全結束,卻在第二天就回警局上班了。謝臻醒來的時候,雨還沒有停,反而有越下越大的趨勢,他是生生疼醒的,止痛藥的藥效早就已經過去,他渾身上下都痛,尤其是腰疼得厲害。
他柔韌性一般,但昨天晚上,謝臻總覺得自己挑戰了人類極限,整個人就差被掰到腿和身子對摺。
靳時雨粗魯、直接到連謝臻的衣服都懶得脫,由此也能窺見結果戰況的慘烈。
火大。
無論是還沒停的雨,還是這場使他們關係更加惡化的冷戰,都讓人火大。
謝臻強撐著想要去洗個澡,勉強正坐在柔軟的床墊上,他盯著地上散落的褲子,不明分說冒出點火氣,他費勁吧啦的給了褲子一腳,卻一個重心不穩,猛地栽在地上。謝臻清晰地聽見腳腕發出咔的清脆響聲,額上頓時冒了冷汗。
他跌在地上,冰冷的瓷磚傳遞出寒氣,瘋狂往毛孔里鑽,他伸出手捂住紅腫的腳踝,心裡自己罵著自己倒霉,又壓不住瘋狂上竄的火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謝臻真心覺得自己之前求的那個簽就是個屁,他這輩子再也不會信什麼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