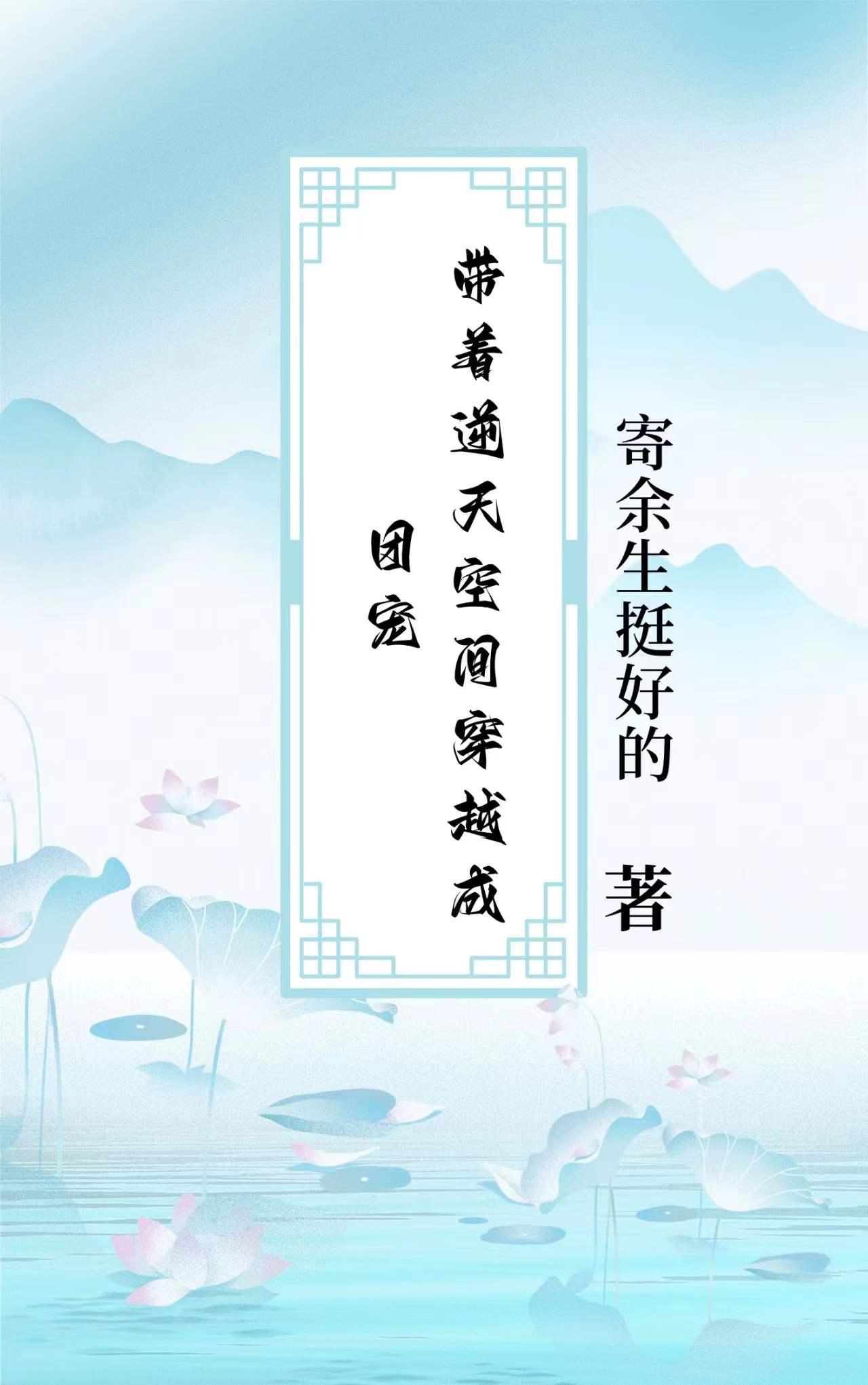69书吧>怎么老是你用英语怎么说 > 第54页(第1页)
第54页(第1页)
朝奉从四尺台上看过来,目含同情。
夏和易装得更加起劲儿了,“我把哥儿托付给乡邻照顾,凑了盘缠上京,老天有眼,竟让我在大街上撞见了他们,可是那负心汉避着我,那家小姐也不是个讲道理的,随手摘了身上的饰就打妾,说是要买断我们夫妻过去几年的夫妻恩情。我……我实在是没有法子了,来时借的盘缠要还,将来还要养大哥儿,碰上这样没良心的人,妾也认了,当了银子回乡,才好——”
“行了行了!”
秋红凶狠瞪起眼,像是不耐烦地打断她,“我们家姑娘好心布施于你,倒还落你一通埋怨了。昨儿你当着我们家姑娘应下的话,可是忘了?”
春翠就一句词儿,努力狠狠“哼”
了声,“当了东西,就别再缠着我们家姑爷了,听到没有?”
夏和易突然不受控地挣脱俩人,往前一扑扒拉上台面,最初只是低低抽泣,后来撕心裂肺地痛嚎起来,“三郎!你好狠的心!好狠的心哪!你丢我们寡母的,将来日子该怎么过啊!我生了你的哥儿啊!三郎,你不要我们娘儿俩了!”
春翠和秋红凶神恶煞地上前来抓她,朝奉不紧不慢地打着圆场,场面一度混乱失控。
夏和易完全沉浸进去了,嚎得正欢腾呢,突然听见楼上“啪”
的一声,听着像是折扇重重拍在桌面上的声音,然后噼里啪啦一连串动静,倒椅子推桌子的,听声儿还不小,木楼梯被踩得吱嘎声和咚咚声并起,最后更是重而闷的一声巨响,像是有人愤怒摔了后门而去。
店堂的人都惊呆了。
夏和易先回过神来,疑惑地抬手往空气里薅了俩爪子,问朝奉:“您这铺子里,闹耗子呢?”
朝奉尴尬地呵呵笑,说:“正是,叫客人见笑了。”
听了说闹耗子,娇主和刁奴霎时间不约而同往店堂空荡荡的中心一缩,仨人瑟瑟抖地凑在一起。夏和易声儿都颤了,勉强维持住平静,“不赶快遣人抓了去?”
朝奉回头张望了好几眼,不知道上面那位是怎么了,虽然不晓得具体名号,但既然能差遣动东家郡王爷的,必定来头不小,心思一乱,胡乱敷衍道:“客有所不知,印子铺专供号神,等闲抓不得,您这话可别再说了。”
号神?耗神?
耗子偷油偷粮的,谁家不是喊打喊杀的,还能有供耗子神的?
大千世界百杂碎,这倒是头一回听说。
夏和易一下来了好奇心,探长了好奇的脖子,“哎?为什么供这个啊?”
朝奉顿了顿,狐疑地望过来。
夏和易心道不好,听着鲜的,一时好奇得过了度,怕要遭怀疑了,连忙收敛起兴奋的神色,继续埋下脑袋持续抖,“在我们乡里,家里出了耗子,都是要即刻逮了去的,不晓得城里规矩,请您勿怪,勿怪……”
横竖两边儿都各自有要遮掩的,盖着布糊弄来糊弄去,各方蒙事儿,待到最终出铺子大门,夏和易还是拿到了不错的价钱。
猫回马车里数了数票子,春翠兴奋得直哆嗦,“姑娘,咱们是不是赚了?”
夏和易眼里的亮光摇曳几下,熄灭了,幽幽叹了口气,“没赚。但凡进了印子铺,能当到原本的一半价,都算是赚大了。再是利用了朝奉的同情心,他们到底还是商人,算起来,这价还是略亏了些。”
泼凉水似的地一思忖,原本的高兴劲儿渐次歇了。
春翠讷讷叹道:“要是这趟能带着地契走就好了,姑娘手里的地产铺子,就是干吃赁钱也够吃一辈子了。”
秋红摆脑袋说不行,“那些可是都登了册入了账的,可别害姑娘走半道上被抓回来。”
三个人面面相觑,所以暂时还是只能靠典当物品凑生计。
夏和易摇摇头,将当票和银票子都小心收起来,“本来该货比三家再出手的,可惜离王爷出还剩四日,实在来不及了,眼下先能凑多少凑多少吧。”
这么一提,瞧一眼车外,太阳都快晃到正当中了,夏和易当即觉得时间紧迫,抓紧往下一家去了。
照旧老路数,先在门外猫一会儿,再回马车上制定作战计划。
春翠已经品出这个游戏的有之处了,兴致勃勃地问:“姑娘,咱们这回扮什么?”
夏和易端着下巴做深沉状,忽然眼前一亮,打了个响指,可惜是个哑声儿的,有些尴尬地收回了手,“这趟不急,先回去梳洗一番再来。”
快马加鞭赶回公府,从暗藏的小路回到房里,梳洗妆扮一阵,三人都穿上府里当季刚的衣裳,鲜绿的色彩,上好的料子,浑身上下挂满了得脸丫鬟才能有的金银饰,挂得像是冰糖葫芦的那根插杆儿,才心满意足,光鲜亮丽地回了印子铺门口。
夏和易回过头,再三叮嘱道:“来,拿出你们这辈子最横的样子,咱们大摇大摆地进去。”
春翠探头眺了眺,缩了缩脖子,“可是这掌柜的看上去不好相与啊……”
“越是这样,就要遇强则强。”
夏和易摆了摆手,“个中道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反正你们看着我就是了,走。”
这家的朝奉,身材高大,满面须髯,肌肉虬结,横眉竖目地扫过来一眼,吓得人都要矮上三寸。
这回夏和易抱来的全是字画。朝奉看罢,皮笑肉不笑地抖了抖脸上的横肉,“好叫姑娘晓得,字画在咱们这一行里都是死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