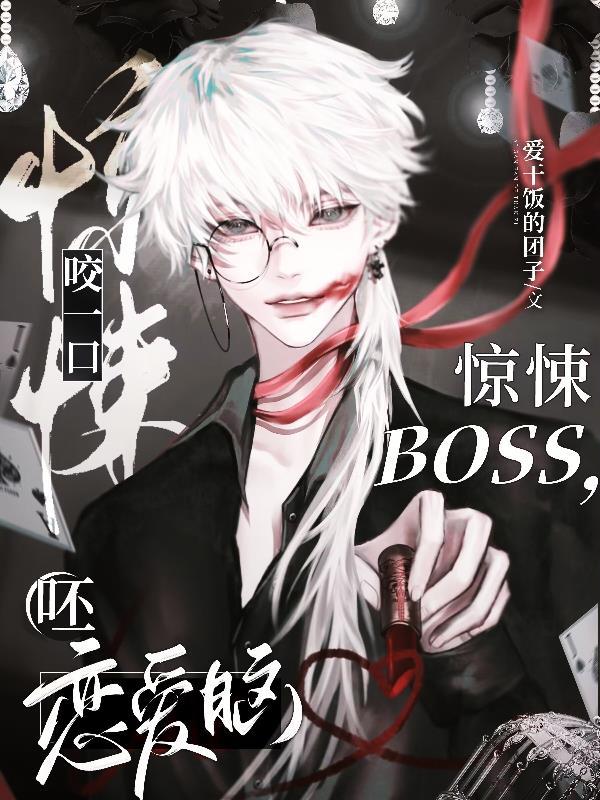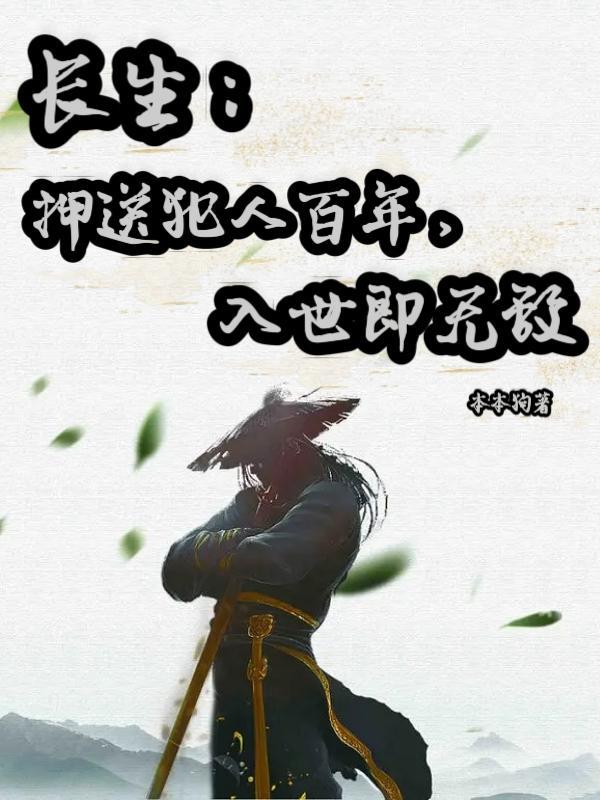69书吧>王妃不想当皇后 海如苏 > 第78章 烛火灭了(第2页)
第78章 烛火灭了(第2页)
“那心儿要做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好,心儿这么漂亮,就是要当皇后,住大房子,吃不完的好吃的,穿不尽的绫罗,戴不完的漂亮簪子……”
母亲没能看到那朵牡丹。
她快要绣完的时候,一朵白色的丧花系到了她的额间。
“母亲呢,母亲呢?”
她哭着往门外走去,跌跌撞撞地摔了好几回。
手磕破了,那朵白色的丧花沾上了点点滴滴的红。
是在屋子的正中间,停了一口棺材。
母亲白着脸,躺在里面,一言不。
睡着了,只是睡着了,一定只是睡着了。
“母亲,母亲……”
她哭着要爬进棺材里,被大人一把抱下。
棺材合上,哭喊着,嚎叫着,大吵大闹,哀求乞怜,都无济于事,她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被泪水迷住双眼的滋味,久违的酸楚,一起涌上心头。
泪光晕开的灯火,好像灵堂上的那一支,江府里,王府里,这样的蜡烛,都是一样的。
明明是火光,为什么冷得吓人?
她好像魔怔了,伸着手去碰那火光,带走母亲的火光,怎么没有把她一起带走?
因为她是要当皇后的人啊,她要做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那样就不用低声下气,就不用受人欺凌,就不用眼睁睁看着至亲离世。
可她不能,她像一只飞蛾一样,连去仰慕牡丹的资格都没有。
蝴蝶能在花间流连,她只能在黑夜里,在黑夜里去寻照不亮黑暗的一点火光。
“元心,元心你在做什么!”
江左川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但她好像被下了咒一般要去碰那束光。
“啊——”
克制着的嘶吼声,烛火在她指尖熄灭了。
江左川拦腰把她抱得远远的。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郑元心啜泣着,靠在江左川的肩上,“到底是为什么?”
“元心你怎么了,生什么事了吗?”
江左川的声音一如既往儒雅,多了些焦急,稳稳地把她揽住。
好像,好像又找到了那个温暖的怀抱,黑黑的,小小的,但能把一切暴虐恐怖都挡在外面。
她蜷缩着,八岁以后第一次试着弱一点,小一点,把所有的不甘,所有的心酸,所有的委屈,所有的隐忍,统统抛掉,涌进那个怀抱。
不必强撑着,不必伪装着,不必防备着。
“左川……”
声音哽咽了,和那个晚上一样。
没有问询,没有指责,更没有怒骂,江左川小心地,尝试着在她身前环成一个圆圈。
他不知道生了什么,也不清楚夫人为什么如此悲戚,但他明白,夫人需要的不是问询与指责,而是安慰与依靠。
或许他从来都不了解郑元心,江左川也承认这一点。他的夫人贤淑端庄,知书有礼,诗酒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通。
但她不是弱柳扶风的美人,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好似一株凌寒而放的红梅,迎着风雪,在悬崖万丈之上,摇曳着,坚挺着。
他没办法看到郑元心坚韧果敢的一面,却能深切地感受到这是她流淌在血液中的,是郑元心隐匿起来的最吸引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