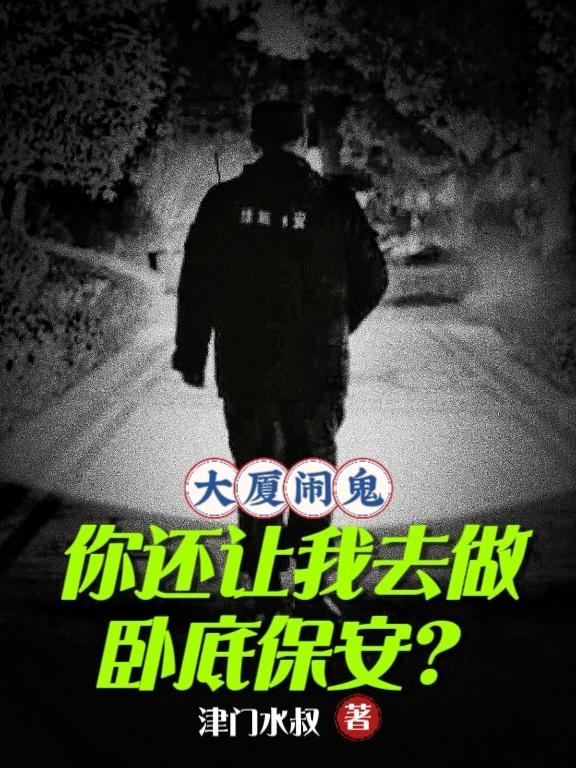69书吧>追风望月 流云落雨 > 第79頁(第1页)
第79頁(第1页)
下午的時候他剛和多蘭一起埋了哈日。好在壩上雖然曬,陰涼處卻沒那麼熱,哈日勉強留了個馬的身形沒有腐爛,埋進了土裡,也算結束了辛苦的一生。
等放完了馬吃完飯,時間已過了八點。他將碗筷難得地交給了多蘭,自己拿了包煙要出門。
多蘭用蒙古語問他:「阿和,要去哪裡?」
他答:「去見一個女人。」
兄妹之間,他以為沒有什麼事是可以瞞著的。
多蘭便問:「是不是幫你帶著哈日回來的那個人?」
「對。」蘇德倒是意外她會知道,「你見過她了?」
多蘭搖搖頭:「只是聽孫成說起的。說你很喜歡她,讓我催你把她娶回來。」
蘇德不置可否,笑笑出了門。
他比跟安蕎約定的時間早了十幾分鐘就到了山上,那會兒天都還沒完全暗下來,他就看清了在當初堆的那個敖包邊上的安蕎。
她身上穿著衝鋒衣,但沒拉緊拉鏈,裡頭單薄的吊帶背心露出來,讓他的喉結不禁一滾,開口問道:「不冷嗎?」
安蕎搖搖頭:「有點,但還好。」
有他在,一會兒不會冷的。他像個火爐子一樣。
蘇德還是看不過去,把自己身上的外套脫給了她。她也沒推辭,套在了衝鋒衣外面。外套上殘存的他的溫度貼在她鎖骨那塊暴露出來的皮膚上,熱燙燙的。
安蕎穿上了衣服,但沒有開口說話的意思。
蘇德的心熬了一下午,不想再熬下去,於是主動開口問她:「你說,有事情要說清楚。是什麼事情?」
安蕎看了眼手機里的時間,笑道:「還早呢,不急。你先跟我說說,這一路上的事吧。」
蘇德深吸一口氣,深深看了她一眼。
她還是這副樣子,笑容像在發著光,落在他臉上的目光都帶著勾子,勾得他無論她說什麼都只想同意。
於是兩人漫無目的地往樹林子深處走起來。
安蕎隨性地問著他,一路上看到了哪些有意思的東西,有沒有吃好吃的飯館。
走著走著,蘇德瞥見從安蕎的口袋裡掉出了點什麼。
他眼神很好,看見那東西是從她手邊掉下去的。她的手就插在口袋裡,沒理由感受不到有東西掉了。知道掉了東西,她卻裝作沒事,大有幾分故意的意思。
於是他也就沒提,若無其事地跟她講路上的經歷。
他不善言辭,說來說去沒什麼有意思的,只講起那個王莉莉,說她其實挺有騎馬的天賦。第一天出去的時候還不怎麼會騎馬,但裴傑和紅髮女一走,她安心地參與起這趟馬背旅行,回來的時候甚至連壓浪都入了門。
要知道在正經的馬術俱樂部里,壓浪起碼得學幾十個鞍時。
王莉莉能學得這麼快,馬術的天賦不在安蕎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