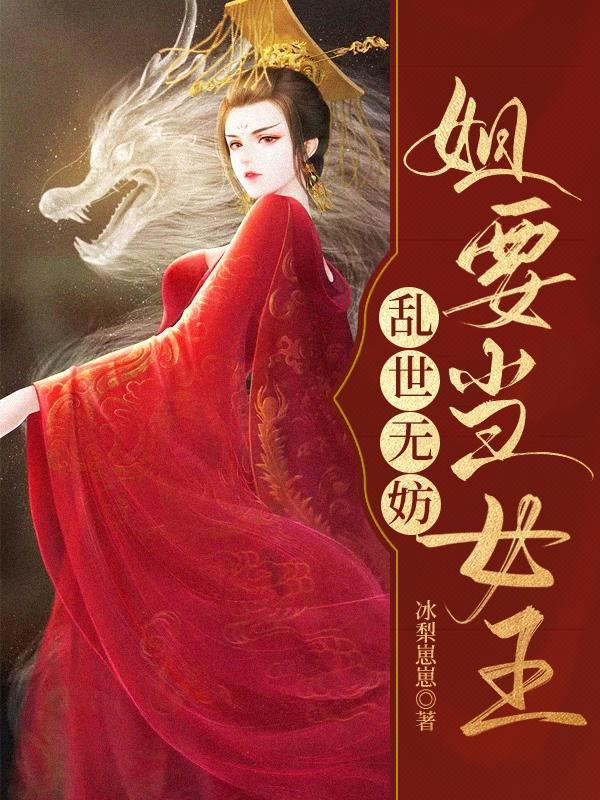69书吧>变形金刚 火种起源 > 第71章 光怪陆离(第1页)
第71章 光怪陆离(第1页)
乌图正在狂奔。他口中不住低吟,一个又一个极寒的咒语释放在面前的海域上,他就这样凝冰渡海。在神风加持下他的度已经空前的快,已经远马车,但他仍拼命压榨着自己最后的精力。
快,快,要更快!还不够……他咬紧牙关心急如焚,汗水刚刚流出就被气流吹干,尽管身后并无追兵。但他不能松懈,这是所有人一起换来的机会,每个人都为此做出了牺牲。
眼前已经渐渐出现冒尖的6地,很好,登6之后马上潜藏,然后再找机会去东境。他忍不住摸了摸腰间的铁球,很快这无上的力量就将隐藏在芸芸众生之间,导师再也别想得到它。
冰凉圆润的触感令人放心,但他摸到另一样东西,一条凹槽。不是装饰用的花纹而是不规则的之字形,就像裂痕。乌图心中激荡,慌忙把铁球拿在眼前,果然有一道裂痕出现在铁球表面上,透过它其中的金色火焰隐隐可见。
这是抛在山石上磕出的裂痕,格莱普尼尔金属可以吸收元素,却比其他金属更脆,从龙脉出逃的时候没来得及检查!
乌图睁大了眼睛,火种显然也现了裂隙存在,它不停冲撞着,球壁上的裂痕不断扩大。随着一声脆响,铁球凌空炸开,乌图被气浪掀飞重重摔在冰面上,不可视的能量波动向四面八方扩散出去,久久都不消弭。
……
连续五个铅丸在导师身上开了数个冒烟的血洞,我端着枪刚想开第六下枪管却“砰!”
地炸开了。雷登临终前把这把昂贵的武器交给我,可惜还是毁掉了,这东西根本不能连。
阴影中导师摇晃着站起来,我弃枪提剑踏步上前。事到如今反抗已经不剩什么意义,扔掉剑等死也是一样的结局,我不可能杀得了他,也不可能杀掉世界上所有的人来阻止他复活。
但我从未感到如此畅快,脑海中说不出的澄明,所有的杂音和质疑都消失了,无论是外界的还是心里的,山谷中只剩陶德粗重的喘息。
长剑刺穿导师的肩膀把他钉在石壁上,我没有杀死他,所以他也没法复活。现火种被带走之后他忽然失去了战意,基本不怎么反抗。
导师垂着头一言不,好像在集中精神分辨着什么,这样的态度让我很不爽。我搜肠刮肚想找几句能刺痛他的话,他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对某个方向猛地扭过头。
“哼……呵呵呵呵呵呵……”
他克制不住地狂喜,不顾肩膀里还插着一把刀就颤抖着低笑起来。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他握住刀身,硬是从血肉中拔了出来。染血的长刀被他丢在一边,他反手掐住我的脖子。
“我改主意了,”
他垂着头把面具贴在我脸上,我刚想反抗心口却一阵剧痛,几乎要昏厥过去,那里被烙上一条漆黑的衔尾蛇图案。“你有资格参加中庭的宴会。带上我的烙印,从此只要你接近至尊的封印就会与我共鸣,我很好奇你会怎样展现自己的落幕。”
他的声音深邃低沉,似乎强压着兴奋。
我摸索着内袋里的折纸刀想要回敬,他却把头贴上来,以一个近乎亲吻的姿势顶着我的额头,刻在面具上的日轮图案仿佛缓缓转动起来,穿过我的瞳孔直达灵魂,接着我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
再次睁开眼睛……不,没有睁眼这个步骤,我甚至没法感觉到自身的存在;但我就是“看”
到了,四周一片荒芜,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不时传来悠长的、鸣笛似的空虚之声。
我不知道在这虚无的混沌中待了多久,也许数万年,也许只是一瞬间,这儿甚至还没有诞生时间的概念。
“真寂寞。”
我轻声说。
虚无中立刻传来无数回音,
“真寂寞”
“真寂寞”
“真寂寞”
……
回音中夹杂着些许轰隆的声音,我有些惊讶,但那声音越来越大,紧跟着迸起炽热的火光。那是爆炸,虚无的许多角落都在爆炸,声音此起彼伏。爆炸持续了好一阵,渐渐平息后留下许多闪亮的碎屑,那是万千星辰。
在群星之间还诞生了另外的东西,它们姿态各异,大部分我甚至根本没法描述它们的外貌,就好比一个图形怎么可能既是方也是圆呢?但在它们身上所有的悖论都被轻易化解。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它们是有生命的,甚至有意识和智慧。
它们在群星间狩猎,有的自给自足,有的彼此吞噬。很快我现那些越能被我辨别的就越弱小,有的是万千触手裹挟的肉团;有的是灰雾遮盖的高大人形;有的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狰狞眼球;有的是一个又一个连接在一起的盘旋星体。
还有的甚至只是一缕光和一团雾,一片潜藏着雷电的黑云,却同样拥有着独立意识。
群星在祂们身边闪烁,彼此吸引,彼此熄灭。
他们或许可以被称为神只,但不会得到任何信徒,因为他们就连存在都太过抽象。我恍然想到几乎在所有文明的传说中神明都是人形或半人形的,但在传说的起点,一切的开端,众神沉睡的时刻从来都是不可名状的黑暗。
众神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制衡,强大的穿行游荡,弱小的抱团而生。祂们甚至还会合作,我亲眼看到一缕光与一条河结合,从中诞生出了类似飞虫的血肉生物。
祂们还会构建和创造,有的神明似乎别具智慧,不断从周遭的星球上抓取材料揉捏成崭新的工具和生命,但最终祂被自己的造物吞噬。
也有神明陨落,但往往祂们的遗体会成为新时代的温床,一位弱小的神坠落在某颗星球上,整个星球的环境因此改变,甚至诞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