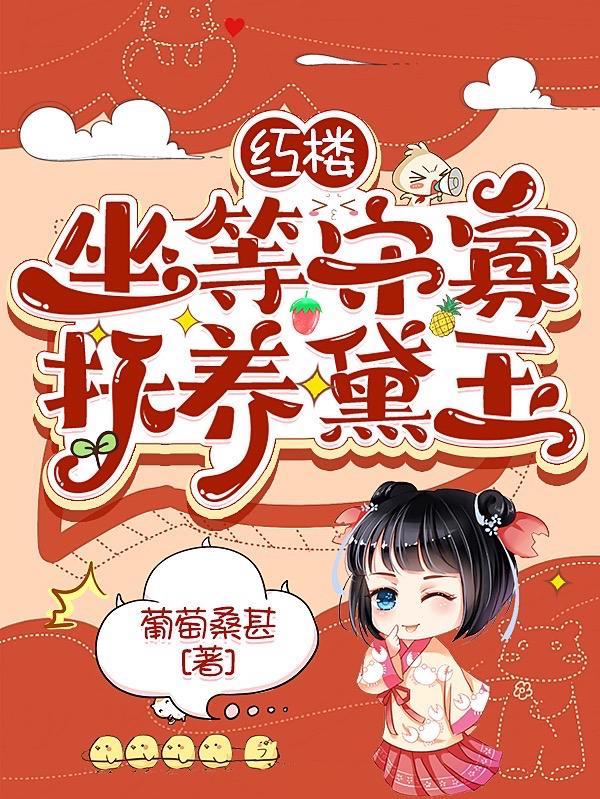69书吧>君心燎月(重生)txt > 第1节(第3页)
第1节(第3页)
夫子被陆迁当众反驳,颇有些不忿,转头再看江眠月,想要数落几句,却发现她面色惨白,唇上几乎毫无血色。
“怎么了?”
夫子见此状,不免有些紧张。
江眠月就算学堂上懈怠骄傲,也有她骄傲的资本,京城书院无数,不是每家书院都能出贡监生的。
三到五年,各州各府才有一个名额罢了,江眠月虽是女子,被选为贡监生,却是实至名归。
她十二岁过乡试,属文一句“爝火虽微,卒能燎野”
(注),惊才绝艳,令人称道。
她的身子若是在这种时候出了纰漏,可不是什么小事。
江眠月醒过神来,顿时觉得小腹坠疼,时不时还有针扎般的痛感。
这熟悉对话,曾经发生过,一模一样……这、这不是她刚及笄过后,在学堂之中,第一次来月信时的场景吗?
她微微垂着头,脸色明显苍白,她手指紧紧捂着小腹,看起来十分痛苦的模样,让夫子颇有些为她担忧。
“你若是身子不适,就先回去休息,过两日便要去国子监考到,切莫误了大事。”
夫子见她虚弱至此,也不恼她不答话,只服软道,“老夫即刻让人送你回去。”
江眠月艰难点了点头。
如她所料,与上辈子一样,这一日她家的马车去城门口迎接从边关回来的父亲,并未在书院门口等候。
而她被搀扶到书院门口不久,陆迁便让家丁驾了马车,殷勤的将她扶上车,要送她回府。
她仰头看着天边斜斜的夕阳,看着面前简单朴素的窄小马车,这正是自己上辈子常常入梦旋即哭醒的场景,心绪澎湃,让她几乎要站不稳。
真的重来了吗?
她居然回到了最开始的时候。
这一次……她不想再如上辈子那般行差踏错,跌落深渊,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马车上的陆迁看着夕阳下发愣的她,止不住的心猿意马。
少女前些日子才及笄,头上还戴着他送的及笄礼……一根桂花枝式样的银簪。
她身着靛青色学袍,明明是书院统一的学袍,简单粗糙的样式,穿在她的身上,却比任何人看起来都要明艳得惊心动魄。
她身形窈窕,却有些瘦弱,此时因身子不适面色苍白,额间满是冷汗,惹人怜惜的同时,可陆迁见她如此,却更让人想将她拥入怀,将她欺负到哭得更厉害才好。
“眠眠,能上来吗?要不要扶你。”
陆迁朝她伸出手。
江眠月忽然听到他喊自己的乳名,有些不适皱眉,此时却无力与他说什么,只摇了摇头,自己踩着凳子勉力上了马车。
从上辈子看来,她这青梅竹马,并非善类。
马车缓缓行进,江眠月无力的靠在马车边,坐在远离陆迁的位置上,静静地看着车窗外。
陆迁的嘴巴仍在说个不停,言语间满是对她关切,可眼眸却根本无法从她的脖颈和脸蛋上挪开。
她心中冷笑,却按下不表,只看着车窗外许久未见过的熙熙攘攘街道景观,任心绪不断起伏。
经过上辈子她才知道,她体质弱,每次月信来时,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最严重的时候,往往会疼到晕厥,人事不省。
从这次及笄礼后的第一次开始,便是次次如此,每个月都要经历一次鬼门关。
可好巧不巧,过两日,便是她去国子监考到的日子。
她此番回到家之后,疼到无法起身,陆迁在这个时候送来了一包药,说是从京中著名的圣手大夫那儿求来的,药到病除,绝不会再痛。
text-align:center;"
>
read_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