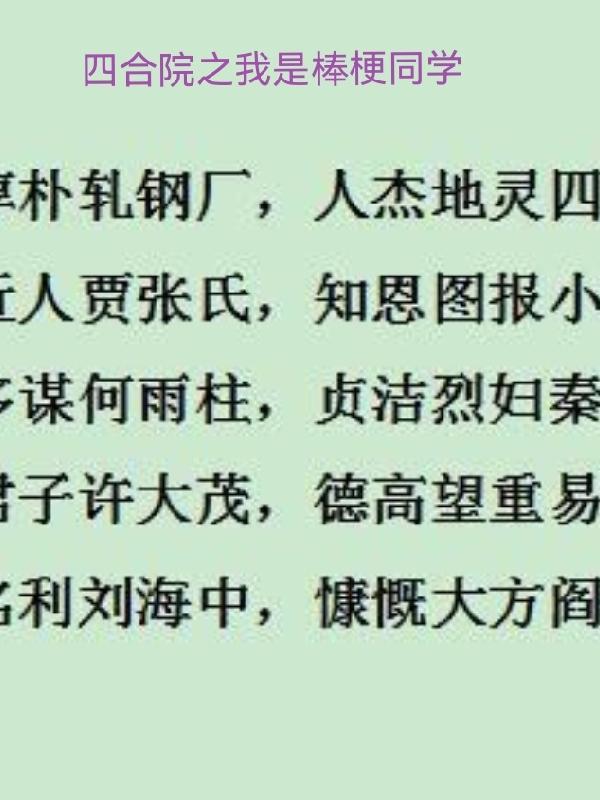69书吧>今晚一起吃饭吗讲的什么 > 第15节(第2页)
第15节(第2页)
程新余:“……”
程新余性子软,不善与人争辩,对峙非她所长。何况对方还是靳恩亭。
她终是败下阵来,眉头紧锁,手忙脚乱道歉:“对不起小靳总,那晚是我不对,我不该招惹您的。我从未肖想过您。您放心,我绝对不会以此来要求您对我负责的。那晚的事儿,我保证守口如瓶,不会对任何人提起。都是成年人了,喝了点酒,做出了点出格的事情,咱们都要拿得起,放得下。您千万别跟我计较,把那件事给忘了吧!”
程新余真是佩服自己。这么一大段话,她一口气说完,居然无比连贯,中间都不带停顿的。
要知道她之前公务员面试,面对那群考官,她可是牙齿打架,话说得磕磕绊绊的。
靳恩亭分明比那群考官恐怖多了。
拿得起,放得下?
把那晚的事儿给忘了?
靳恩亭都要被气笑了。她倒是说得轻巧!
他的脸黑得彻底,眼神凌厉非常。
他棱角分明的脸偏了偏,看向窗外,路灯昏黄的光线摇摇晃晃,千丝万缕,灯下夜雨翻涌。
靳恩亭不免想起在程新余家醒来的那个清晨。
也是这样的雨天。细雨铺天盖地,铺成一张绵密混沌的网。广玉兰宽厚的叶片上挂了一层薄薄的水,悄无声息地滑过清晰的脉络,一滴滴往下掉,湿溻溻轻响。
始作俑者已经逃了,在他醒来之前。
他的生物钟一向准时。那天却失效了。他在八点钟才苏醒。
地板上四处散落的衣物,昭示着昨晚在这间屋子里的疯狂行径。
靳恩亭捞起自己的衬衫和西裤穿上。踩着拖鞋去了阳台。
阳台上横着两只大纸箱,霸占了空间。他险些被它们绊倒。
箱子没用胶带封上,箱口赤喇喇地开在那里。他低头一看,发现箱子里装的全是考公的试卷和复习书。
他想起程新余昨晚在餐桌上的话。四年考公失败。难怪会有这么多资料。
她昨晚失控,失恋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
考公失败,爱情破灭,这姑娘未免也太凄惨了一些。
靳恩亭盯着那两只大纸箱,后背抵住阳台边沿,低头为自己点了根烟。
空气里的烟圈寂静散开,他抽得很慢很慢,像是有满腹心事。
他不爱烈烟,烟的味道极淡。烟雾压进肺腔,照旧解不了内心深处的焦躁。
一直等到九点,程新余也没回来。
他知道她是打定主意不回来了。
他活了三十二年,头一次感到荒唐。不是因为他和程新余睡了。而是因为她不告而别,没留下只言片语。
他觉得自己被人白。嫖了。
——
气氛凝滞,近乎诡异。程新余看着靳恩亭越来越黑的脸,她的腿开始不受控制的,小幅度抖起来。
她强行摁住,在心里骂自己没有出息。
要怪只能怪他气场太强,在他面前,她总是底气不足,怂的要死。
她言辞恳切,句句发自肺腑。有哪点说得不对吗?
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小靳总,我不妨跟您说实话。招惹到您,我罪无可恕。其实我是有想过辞职的。第二天一早我连辞职信都写好了。可我现在真的好穷,没存款不说,这个月还要还三千多的花呗,我要是辞职了,我连花呗都还不起了。而且我还要交房租,还要吃饭,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花销……”
程新余狠狠地抹了把辛酸泪。
靳恩亭:“……”
她见他这么生气,心中越发没底。她只能换个法子。试图用自己可怜凄惨的近况来唤起资本家为数不多的良知。
“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过我?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您放心,等我手头宽裕了,我马上辞职回老家,保证离您远远的。”
靳恩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