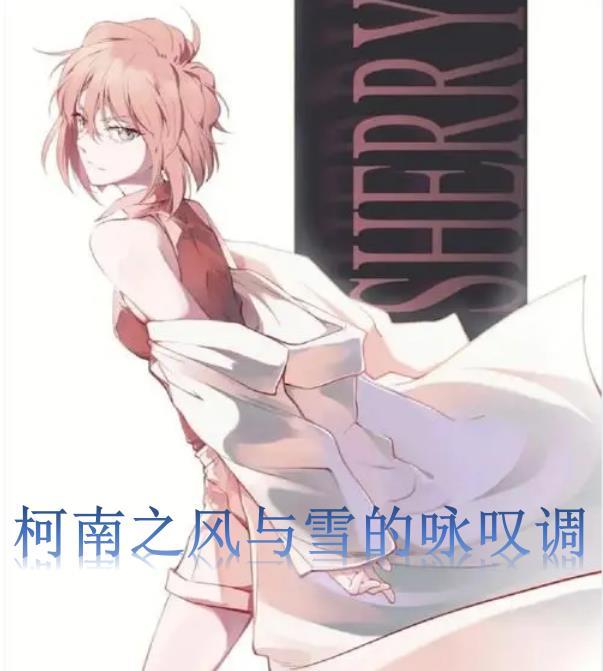69书吧>旧春闺好看吗 > 第五十章 朋党比周(第2页)
第五十章 朋党比周(第2页)
四周的垂緌因而显得愈刺耳起来,一声一声地,直要把人的脑子翻江倒海一番。
过了很久,他才在连绵不绝的虫鸣里找到自己的声调,“你说得极是。”
沈南宝也好不到哪里去,堂堂指挥使,威严赫赫的一人物,旁人都不敢直视亵渎的存在,她却离得这么近,近得可以看清楚他眸子里倒映的自己。
她暗自赞叹着他朗朗如日月的相貌,这么近都还恁般精瓷得无可挑剔,却又惶惶害怕他听清楚了自己擂鼓似的心跳,不由得开了口“殿帅既如此特地前来寻我,必定是有要事,那么殿帅不妨说一说,我洗耳恭听便是!”
她虽打定了主意要装腔作势,但萧逸宸到底是上阵沙场见惯了刀光剑影,在这样惊心夺魄的时候也能够处变不惊地听出她语调里些微的失措。
也因而,方才被她打乱的姿态瞬间拉了回来,他又操起那一副漫不经心的笑貌,“五姑娘忘记自己先前说的话了?”
先前说的话?
什么话?
绿葵?
沈南宝恍然的瞪大了目。
萧逸宸笑了笑,抢在她先前说了话,“五姑娘既记得,那便别忘了端午出来,我带五姑娘去瞧瞧龙舟争渡。”
京畿不啻河北一带临近渭水,能纵水飞跃千里,让人观摩那恢弘的气势,多是三帮会聚江河,伴着敲锣打鼓,几经竞赛方决出胜负,不过即便如此,仍是引人入胜。
前世沈南宝随陈方彦去过一次,因着人多势众,水西门外的楼台还不堪重负塌陷了。
今世的话,若不出她所料,她应当是出去不得的。
沈南宝颇有些头痛,要是早知道能借萧逸宸的手,她便不必要让‘绿葵’在彭氏跟前晃悠,引她们出洞替自己去寻绿葵。
如今祖母将她视为大敌,又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哪里能允准她胡乱出去。
她轻轻翘了唇畔,弯出无可奈何的况味,“殿帅,您这不是为难我么?我怎么能出去,你……”
“五姑娘足智多谋,还会被这点小事所难倒么?”
萧逸宸垂下眸,视线落在那伶仃的柔荑上,尖尖的指尖戳进了他的心窝似的,他不经意地生出一丝狎戏的兴致。
“不是五姑娘说得么,你是我的半个谋士。”
沈南宝此刻几乎想咬掉自己舌头,她这算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了么?
明明自重生以来,她和谁相处都如此游刃有余,为何和他总是如此颠踬,全然没有一丝往日的从容。
她闭上眸,深吸一口气。
耳畔有狂风骤起,吹动树叶如旌旗猎猎作响,她在这样鹤唳之际睁开那双琉璃的眸子,看着萧逸宸缓缓点头。
她看到他稍侧的目光含着一丝冷冽,翣眼的瞬息,他直起了身子,主动退让开来。
“那我便翘以盼,端午那日五姑娘登靖水楼,与我会晤了。”
新鲜空气的涌进,让沈南宝终于能够如复以往的喘气,而他还是那样端然独立,颀长的身子在阑珊的光影里挺拔如松。
也不知道他视线流连在哪儿,但沈南宝还是觉得两相对立实在有些尴尬,遂屈了膝,“殿帅,我出来甚久了,得回去了。”
萧逸宸负着手,站在黑漆漆的树影下,并没有拦她,“也是,再待得久,只怕到时候五姑娘及笄了只得等着我上门来提亲了。”
提亲,又是提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