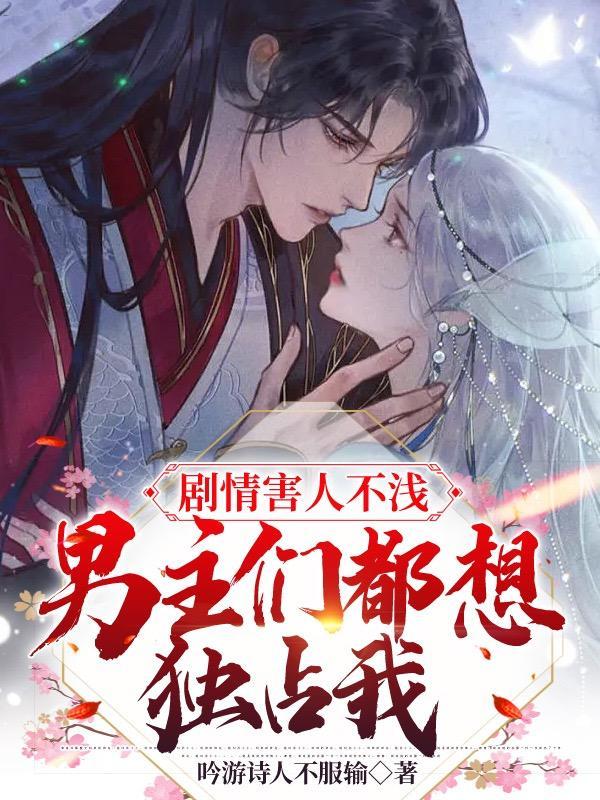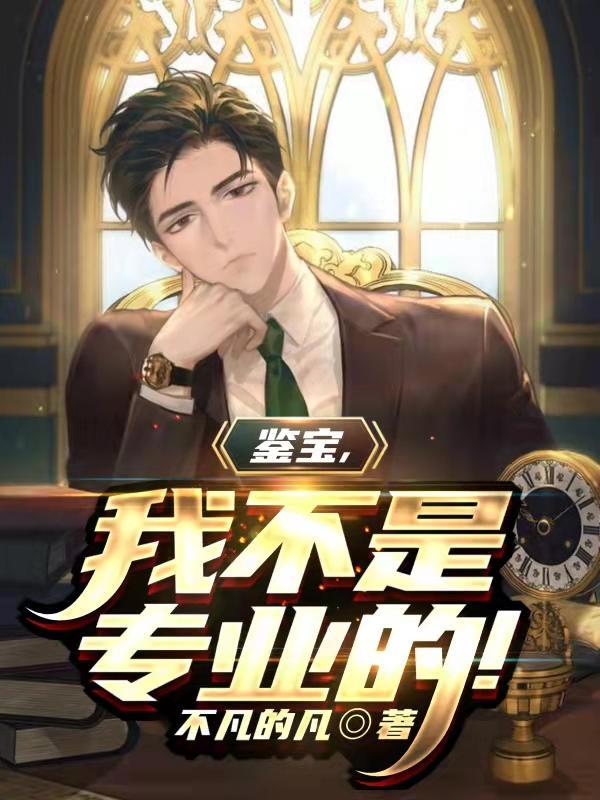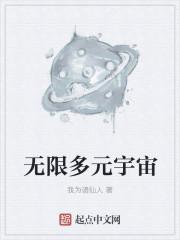69书吧>明宫小食光番外 > 第47节(第3页)
第47节(第3页)
等到除夕前一日,两人难得有了空闲。朱祐樘虽不必上朝去,但习惯使然,仍是早早的就醒来了。
他这一向虽然忙,但心情倒还不错,是寻到了舅舅们,心里的那一块执念被补全的缘故。
那日与舅舅们说话,虽语言不通,但他们的乡音,倒是勾起了朱祐樘对娘亲的怀念,她唱歌的时候,就是用得乡音。
朱祐樘问纪旺与纪贵,家乡可有与藤、树有关的歌?纪旺便唱了几首,听到第二首的曲调,朱祐樘很有些激动,就是这个旋律,那时候娘亲唱的一定是这个歌。
他便跟着两个舅舅学唱这首歌,一句一句的学,也学会唱了。
笑笑还没醒,朱祐樘撑着一只手看着她,心里回想着藤缠树的曲调,想等一会儿唱给她听。
可是等了一会儿,张羡龄仍是沉沉睡着。
朱祐樘看了一眼天色,有些无奈,今日虽不用上朝,但要给太皇太后与皇太后请安,还是要叫笑笑起来。
张羡龄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见一阵歌声,昏昏沉沉的,以为是穿越前设的闹铃。她睁开眼,瞧见睡帘,忽然反应过来,是朱祐樘在低声歌唱。
他唱歌的声音很好听,张羡龄静静地听完,笑起来,两手使劲的鼓掌:“唱的真好听,这是什么歌呀?”
“藤缠树。”
朱祐樘道,“小时候娘亲教给我的,后来忘了,前一阵子又重新和舅舅学了一遍。”
听了这话,张羡龄倒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她只是有些庆幸,幸亏覃吉在年前没将结果查出来。
第62章
弘治二年的春节,倒是个暖春。
明晃晃的日光照在大袄上,竟然有些热,张羡龄便没穿披风,只是外罩了一件雪青色比甲,已然是作春装打扮。
鞭炮是从大年二十九就开始放了,每隔一个时辰,必定噼里啪啦放一串。万岁爷走到哪一宫,后头也是满殿红色鞭炮纸。
喜庆是喜庆,吵也是真吵,张羡龄索性将冬日戴的暖耳翻出来,当作耳罩戴在头上,以减轻些烦人的鞭炮声。但暖耳戴在耳朵上,捂着又热,幸亏梅香和秋菊连夜赶制出了一对耳塞,张羡龄方才清净了些。
考虑到年幼的亲王与公主也许会被鞭炮声惊着,张羡龄又命小宫女做了十来副耳塞,送到抚养亲王与公主的老娘娘宫中。
等到正月十五,乾清宫前早就安设好了鳌山灯,好大一座灯,足足有乾清宫屋檐那么高,自下往上用苍翠松柏层层堆垒,绿叶构造的灯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各色彩灯,其上还有八仙与佛祖等神佛的塑像,气势恢宏,纵使是白日所见,张羡龄也为这鳌山灯所吸引住。
听说这样的鳌山灯除了乾清宫广场的这一座外,宫门前也会有一两座,以供百姓赏玩。
至正月十五,张羡龄与朱祐樘往清宁宫去,给周太皇太后行礼。
今夜是家宴,清宁宫前殿摆了好几桌酒席,地上铺着大红百花图毡毯,依次列着各色食案,也有紫檀雕花的,也有剔红刻福字的,看着就是新春富贵。
周太皇太后辈分最高,又是在她宫里,自然坐主席。朱祐樘坐在左侧首席,右侧首席乃是王太后,接着才是张羡龄。
众人入席,互道了祝福,便添酒开宴。
为了给周太皇太后解闷,清宁宫殿前的月台上搭了一个戏台,此时殿门齐开,灯火辉煌,坐在殿内正好可以瞧见戏台。
张羡龄倒很有些好奇,今夜会唱什么戏呢?这个时候,京剧都没出现了,也许会唱昆曲?可赫赫有名的戏曲家汤显祖这时候似乎还没出生,想来像《牡丹亭》、《南柯记》等经典曲目也未问世。
一旁的王太后见张羡龄频频盯着戏台,便笑道:“今夜应该有内侍阿丑演的传奇,他演戏一向好玩的。”
传奇么?张羡龄听着这名字有些陌生,似乎是比昆曲更古老的曲艺,便决心好好看一看,不忙着吃点心。
乐声响起,一个中年内侍踏着鼓点走上戏台,正是钟鼓司佥书阿丑。
他大摇大摆走上台,步伐怪模怪样的,手里还握着一执板,还没开口说话,已经逗得不少老娘娘嘴角上扬。
text-align:center;"
>
read_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