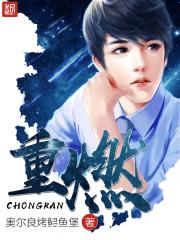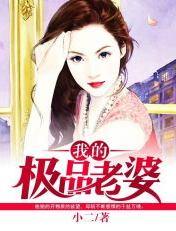69书吧>工出头是什么字 > 第4章 末代万元户(第2页)
第4章 末代万元户(第2页)
堂伯经常下海捕来的野生小黄鱼,从上一年开始腌制,赶在次年春节前,从陶土瓷缸里挖出来,把咸鱼上的盐巴抖落干净。咸鱼拿去卖,抖落下来的每一粒盐巴,都要收集回瓷缸持续套用。
堂伯说,盐和大米,在当年都属于国家重点保护且定量供应的、防“走私”
的贵重物资,不能浪费。
他和婶婶在严冬酷寒里,经常要三更半夜动身启程,徒步翻山越岭,用一根沉重的扁担,轮换着把两大箩筐的咸黄鱼挑到鹿城市里去卖,最好的价钱仅卖过一角五分钱一斤。
“呵呵,比大米还贵了一分钱呢!”
堂伯和婶婶当时都乐得不行。
可想而知,那时候的一万元,来之不易,花销也不易。不知道能买多少吃的用的,能办多少的人生大事。
令堂伯始料未及的是,短短几年时间,那些他曾以为已然“高价”
的野生小黄鱼,会成为濒临灭绝的“小金条”
。如今既是“天价”
,也难得一见了。
就唠叨会我自己记得最清楚的状况吧。
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每个学期的书本费,加加起来,总不过o。5元。报名费是二年级1。o元,三年级1。5元,四年级2。o元,五年级2。5元。
五年来都是循序渐进,5毛5毛的涨,从不胡乱跳跃。可到初中那年,就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初一五十,初二一百,初三两百,到高中。。。唉,不提也罢。
再说邮票,从o。o2元开始涨,一直涨到o。1元,加急的o。2元,甚至o。5到1。o元的都有。到九十年代,干脆连寄信都用快递了,邮票反倒因此演变成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天价”
收藏品。局时,我们七十年代的穷命人,又早早地失去了最佳的收藏年份,与“天价”
的财机会失之交臂。
想起来就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些“万元户”
叫屈,来如潮涌,去若潮退,太不容易了。
我在网上搜索过这样一则报道,1979年2月,比新中国出生年月还早的党报——人民日报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了一个叫“黄新文”
的人的事迹
‘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o7万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59oo多元。。。’
黄新文,就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
。在改革开放初期,黄新文也是全中国数亿农民羡慕妒忌恨的“万元户”
。
当年《人民日报》的宣传效果和影响普及力并不逊色于如今互联网,一时间,全国各地或亲临、或去函,向黄新文请教致富经的人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
可现在,还有谁记得到他呢?
那个时期的万元户,基本上都是全靠一把锄头一双手在土地里刨出来的。
所谓的家庭副业,不是养鸡养鸭养鹅,就是养猪养羊养兔什么的,全是自然生产的草科植物或草籽能养活的牲畜。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养殖户们就种“高产”
的红薯等块茎农作物来展养殖业。
究其致富根源,仍旧是以土地的产出为主。而那时的土地怎能堪比如今的寸土寸金?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
尽管那些钱来得那样的不容易,当年仍旧有少数的嫉富又嫌贫的闲人认为
农村的万元户都是些不良“奸商”
,甚至还有人把农村万元户的出现同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出现画上等号,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广泛的讨论,甚至躁动。
我看到这些言论时,就觉得每个时代都必须有这样一种“巴不得又来阵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运动,把万元户迅增长的势头给掐住”
的人群,才不至于让日后的贫富差距拉的如此之大。
不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世界永远不会被灭绝的,恐怕就是那些以财为理想以致富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人了。何况那些亦步亦趋跟着党走的敦厚老实的农民“万元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