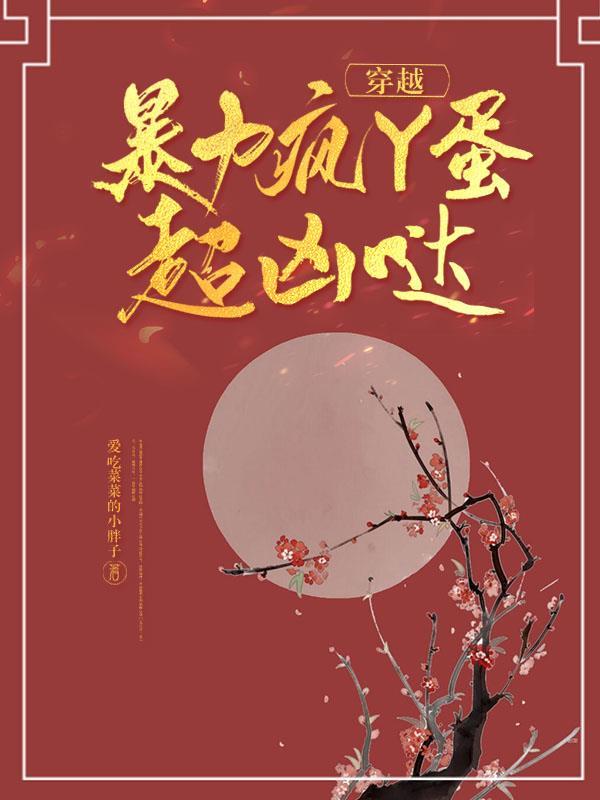69书吧>猎户家的小厨娘 蜀国十三弦 > 第38节(第1页)
第38节(第1页)
沈晚夕眼睛涩了涩,泪珠便在眼眶里打起了转儿。
她蒙着眼睛想,阿娘,我是不是不完整了,呜呜呜……
云横推门进来,端了一碗从钟大通家顺过来的雪梨粥,热乎乎的还冒着热气。
看到气鼓鼓、哭唧唧的小姑娘,他伸手便将她抱起来,靠在他臂膀,“喝点梨粥,对嗓子好。”
沈晚夕噌的一下脸又红了,这是在笑话她昨晚嗓子喊得哑了?
大部分时候,分明都是他用手指按住她唇角,再用他的唇将她堵得死死的,不肯她哼得太大声。
姑娘小脸红得像是春日里上了桃花妆,在日光下晕出耀目的光影。即便是头发凌乱,面容也看着憔悴不少,可在云横眼中,她就是漂漂亮亮的,娇滴滴的小姑娘。
他看着她娇妮的神态出了神,想到昨晚她笨手笨脚地亲他,吃了又吃,最后动作比他还要熟练,不由心痒难耐,恨不得再狠狠要她一次。
可现下看到她红得像兔子般的眼睛,想起她在他身下受不了时,那嘤嘤啜泣的委屈模样,他又心疼起来。
他的小姑娘啊,恨不得当心肝一样疼,想揽她在怀里一辈子都不放开。
云横骗着哄着喂她喝下雪梨粥,总算将这副辘辘饥肠填满一些,沈晚夕跟着才恢复了一点体力,嗓子也润了润。
花枝像是提前知道什么似的,约莫申时才跑过来,斜挎的小竹篮里放着一些边角料的肥膘肉。
沈晚夕前几天刚刚提过想要买一些便宜的肥肉回来熬制油渣,花枝便记在了心上。
在厨房里摸爬滚打的人原本不厌恶这样的食材,可今日沈晚夕刚见到那一篮皮下的肥膘肉,心里登时泛起了恶心。
也有可能是昨晚喝了点酒,肠胃不太舒服。
花枝冲她眨了眨眼,笑道:“我怀着身子害喜,是有些见不得这些东西,可嫂子怎么也这样?难不成嫂子也怀上了?”
沈晚夕忙伸手半堵上她的嘴,轻嗔道:“你别胡说,我昨晚才——”
她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时候,花枝已笑得浑身发抖了,“昨晚才怎么样?”
沈晚夕又羞又气,她怎么这么笨呀!又要被花枝取笑一段时间了。
她将自己好好收拾了下,围上围裙就到厨房处理那几块肥膘肉。
其实肥肉并非不受欢迎,村里人平日里买不起肉,可又馋荤腥,只能趁着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才回买点肥肉回去,或是每道菜里放一些,或者扔到锅里生火慢慢熬,逼出猪油和小块的油渣。
猪油炒菜极香,油渣亦是庄稼人眼中的珍馐美馔,放到素菜、豆腐里瞬间能香出好几个度,比直接吃瘦肉还好吃。
灶膛里生了小火,锅沿冒着热气,沈晚夕将腌制后的肥膘肉扔下锅,锅中顿时冒出了滋啦滋啦的响声。
待锅中水蒸发干净,一块块的肥膘肉就慢慢渗出油来。这时用锅铲不停翻炒几下,让肥肉充分接触锅底,直至油渣微微泛黄,满屋都溢出了浓郁的肉香。
沈晚夕嫌呛人,又怕呛到花枝,直接将厨房的窗户大开,把外头的风放进来,也把屋里的香味儿散了出去,一时间整个村子都弥漫着浓香的肉味。
素菜再美味,也不及肉味带给人的欢愉。
沈晚夕将熬好的油渣捞起来的时候,自己不犯恶心了,花枝也不害喜了,两个人闻着香味,鼻尖都像是在跳舞。
刚刚熬好的油渣金黄酥脆,不算太嫩,也不会太枯,几乎每一块油渣都有一丁点炸焦的瘦肉,呈现出诱人的焦黄色,油渣里头被炸得蓬松极了,咬一口下去嘎嘣脆,香得人浑身的骨头都麻了。
两人边炸边吃,丝毫不腻,不自觉地已经吃了不少,停下来时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认不得连手指头都要刷一刷。
熬制完后,沈晚夕将锅里的猪油和油渣分开捞起,最后锅中留下一层舀不上来的猪油,她便扔了绿叶菜下去炒,最后连不起眼的蔬菜都香入了骨髓之中。
晚饭她又做了一道油渣豆腐羹,香嫩柔滑的豆腐中嵌着零零碎碎几块炸好的油渣,登时肉香弥漫,令人食指大动。
沈晚夕洗净了手,将油渣分成两半,一半同钟家分食,另一半打算明早送到客满楼去,这种油渣无论如何都是用得着的,指不定掌柜的尝过之后还能卖个更高的价钱。
饭后,花枝给她说了说村里的事,提到阿萝时不禁露出鄙夷的目光,“小嫂子不知道,咱们没见到阿萝的那几天,听说她夜里做梦被人扼住了喉咙,醒来时脖子红肿了一圈,还有五个手掌印,吓死人了。”
“啊?”
沈晚夕低呼了一声,这是被鬼压床了么?
![女道君[古穿今]](/img/1495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