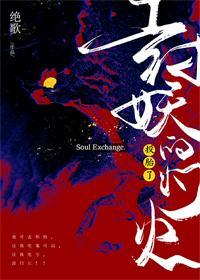69书吧>山海间温泉度假区 > 第1节(第2页)
第1节(第2页)
邵景行站在阳台上,把下面众人的神色尽收眼底。没办法,他视力太好了,就算打游戏看电影玩手机用电脑,视力至今还是5。2,没半点要近视或散光的意思,也就看得格外清楚。
其实不用看,他也知道这些人会是什么反应。这一院子的人都说是他的朋友,其实九成九都是狐朋狗友。他们愿意来,是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有个能干的叔叔,也因为他特别“二”
,好占便宜。
至于说真正关心他,会把他说的话当个事儿的?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不过邵景行也没指望这些人的关心。他就是宣布一下决定,免得等明天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再被人当成醉驾意外什么的。他是没法选择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但至少如何离开这个世界,他总得自己做回主。
自杀的事情没有后续,自然是很快就被所有人抛在了脑后,派对依旧热闹地又进行了两个小时,终于在凌晨一点结束了。
其实这个时间对于夜生活来说还很早,但熟悉邵景行的人都知道,景少要睡美容觉,不熬通宵。
不过爱睡美容觉的景少现在并没有去睡,沐浴之后他反而又换了一身衣服,甚至比刚才派对上穿的那一身还要精致些。然后他走进书房,打开了写字台上的一个抽屉。
书房这个东西放在这座别墅里就是个笑话。别管那些书架和书看起来多气派,其实要不是有人打扫,这上头都能落满了灰——景少才不看书呢。学历都是去国外的野鸡大学混出来的,而且一毕业他就发誓再也不翻书本了——说起来,跟他随口发过的无数条誓相比,这条誓言他倒是履行得很彻底。
所以书房这个地方是别墅里最没用的地方,就算有什么重要东西都不会放这儿来,因此也就没人会想到,这写字台的抽屉里放的,居然是碧城集团全部财产的处理方式。
邵景行把捐献和转让的文件又翻了翻,其中那些繁琐的条款他根本就没细看。对他来说,只要保证等他死了之后,他名下的所有财产不会被还在世的亲人继承去,那就够了。至于这其中别人坑了他多少,最终捐出去的又是多少,他不在乎。
不过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才能毫无痛苦又迅速地自杀呢?
邵景行按着右肋隐隐疼起来的部位,艰难地思考。
虽然按照他查阅的资料,他肝部生长的那东西还只是带来了初期的疼痛,但他已经觉得要受不了了。这也是他放弃治疗的原因——已经是中晚期了,医生倒是说还可以治一治,但他听得出来,医生也没有把握说一定能治好,更大的可能是他受完了化疗的罪,病情还是无可逆转地恶化,直到……
听说这个病到后期会很疼。邵景行是娇生惯养大的,他不能接受那种打着杜冷丁止痛的日子,所以他想在疼痛明显之前,就先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怎么结束呢?
安眠药是不行的。想要一睡不醒,他得吞几百粒,吞到最后,单是要把水和药片咽下去就会很痛苦了。
跳楼?他恐高。
跳海?淹死据说比上吊还要痛苦,而且时间会拖很久。
安乐死?对不起国内不提供这种服务。要去国外执行则很麻烦,估计没等他上飞机,就会被他叔叔发现,揪回来送进医院化疗了。
枪击倒是比较好的,但邵景行是个遵纪守法的人,他没枪。
邵景行赫然发现,虽然他做了这些年的纨绔,其实都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连开车违章都没几次,以至于现在让他用什么非法手段搞点东西,他都觉得很为难。
想来想去,也许只有撞车方便快捷了。
高速行驶的车辆,冲撞时产生的巨大力量能够瞬间把脖子折断,一下子就完了,也许连痛苦都感觉不到。而且这个不比跳楼,他恐高,但是并不怕飚车。
邵景行就是抱着这种想法,驾着他最心爱的红色小跑车离开别墅,驶上了最近的一条高速公路。
这个时候,路上的车已经很少了,这正合邵景行的意。他不想撞别人的车——自己想死,干吗要连累别人呢?还是撞护栏比较好。虽然这样国家会有损失,但他把财产都捐了,也足能抵得过这点小损失了。
不过计划这种东西,总是没有变化快的,邵景行还没有把车加速起来,就有一辆黑色别克商务车从对面逆行过来,猛地撞上了他的车。呯地一声响,两辆车打着转停在了路边。
邵景行被转得晕头转向,要不是他素来有系安全带的好习惯,这一下非撞得鼻青脸肿不可。他正想愤怒指责一下对方司机逆行的违章行为,就听又是呯地一声,贴着保护膜的车窗玻璃四散飞溅,黑洞洞的枪口已经伸进来顶在了他头上:“下车!”
邵景行昏头昏脑地被拽下车,又被塞进了商务车的驾驶座。
他才坐进去,就闻到一股血腥气。从驾驶座艰难移到副驾上的司机右肩衣服都被血浸透了,脸色也发白,但这并不妨碍他用凶恶的眼神盯着邵景行,还晃了晃手里的枪:“快点开车!”
而刚才一枪把邵景行车窗打碎的男人则坐进后座,顺手把旁边的什么东西一推,呯一声关上车门:“往前开!不然崩了你!”
“你,你们——”
邵景行哆哆嗦嗦地发动车子。这会儿他已经听见了后头传来的警笛声,警车的红蓝车灯倒映在后视镜里,还有人在拿着扩音器喊话:“前面的人立刻停车!你们是逃不掉的——”
“老子有人质!”
后座上的男人猛地把身边的孩子拉起来,逼迫他把头探出车窗外,“你们再过来,老子把几个小崽子全杀了!”
邵景行这才发现,车里还有三个孩子。歹徒手里的小孩有五六岁的样子,头无力地垂着,仿佛在生病,即使被粗暴地拉拽着也没精力挣扎。另外两个稍小点的孩子是一男一女,都被反绑着两手扔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嘴上贴着胶布,只能发出小声的啜泣。
有人质在手,后面的警车也不敢靠近,只是不停地喊话:“……孩子在生病,你们再耽搁下去,这件事的后果将十分严重!现在释放人质,可以从宽处理……”
“从你妈的宽!”
副驾上的歹徒骂了一句,用枪管戳了一下邵景行,“快开车!”
“我,我不开。”
邵景行被他戳得肋骨生疼,却反而松开了离合,“你,你们怎么能绑架小孩子,还是生病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