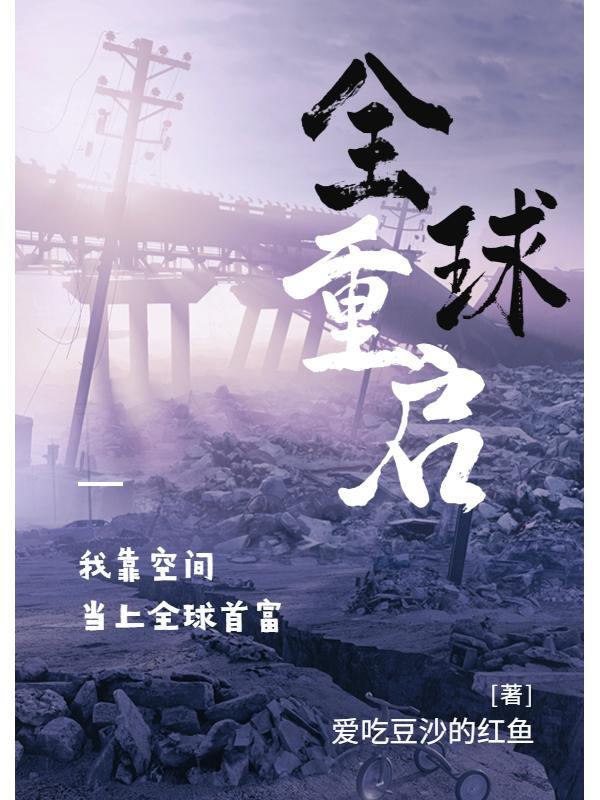69书吧>含情目怎么解锁 > 第22节(第3页)
第22节(第3页)
那是安德头一回听戏曲。
傍晚,他处理完公事,从社区出来,走着走着,便来到一家花店前,问老板娘买了一束白玫瑰。
他捧着花,一路步行到滨城大会馆,途中全是朝他行注目礼的路人,但他没有任何感觉,全凭本能地拿着已经快被自己翻烂的门票,进入活动演出大厅。
里头鼓乐喧天,座无虚席,他绷着张脸,沉默寡言地坐在人群中,听完童音大合唱,东北二人转,女子民族舞,玫瑰的主人终于出现了。
八尺戏台上,薄云漏月秀屏开,玉梅入风春色来,王文音踏着仙人步伐,舞起水袖,一个云手,一个盘腕,一个转身,几步圆场,青衫鼓荡,水袖轻颤,亦真亦梦……咿咿呀呀唱尽杜丽娘的一腔心事。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缱绻。
安德幼时在国外天天被西方歌剧熏陶,哪里听得懂多少戏曲唱词,他不过是爱她的一嗔一喜,一笑一怒,一娇羞。
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他终于明白,那天与她意外邂逅,为何没有向她道破实情,拿回属于自己的吊坠。
一切不合逻辑的行为背后,只是因为一个如此简单的动机。
那场义演最后大获成功,主办方筹到不少灾区募捐款。
王文音下了台,在化妆室里对镜卸妆,会馆工作人员捧着一束白玫瑰进来,站在她身后,笑道:“文音小姐,有位先生让我把这些花送给你。”
王文音摘下头上珠钗,从镜子里瞥了眼温润优雅的白玫瑰,略有欢喜道:“那位先生……姓陶吗?”
“哦,不是。”
工作人员摇头,“他说他叫安德。”
“这样……”
王文音神情寂寞,从唇边挤出一丝微笑,“你把花放到桌上吧,谢谢。”
她卸完妆,有些失神地望着左脸上的胎记,片刻,释然地深吸一口气,起身换回常服。
工作人员从化妆室出来,跟等在走廊里的安德说:“先生,花已经送进去了。”
安德背靠墙壁,手里灵活地把玩着一枚徽章,闻言微微颔首,表示感谢。
工作人员离开后,他又继续等了半个小时,王文音终于收拾好东西,捧着花出来。
他直起身,转头,视线落在她左脸薄红的一片胎记上,神情闪过一丝错愕,却仍旧无法控住地迈开步伐走向她。
就在这时,王文音突然眼神闪躲地望着他身后,微微一笑,柔情似水地喊了声:“常宁。”
安德猛地停下,仿佛一只被困在荆棘笼中的猎鹰,沉默不语,一动不动。
陶常宁快步从他身旁经过,走到王文音跟前,亲昵地搂过她的腰,与她小声寒暄。
“抱歉,今天有点急事来晚了,没能欣赏到你的表演。”
“没关系,下次单独跳给你看。”
“那可说好了,只跳给我一个人看,不许反悔。”
“放心,我没有骗人的习惯。”
“这才差不多,对了,这些花是谁送的?”
“哦,是一位……戏迷。”
王文音睫毛轻轻扑闪,弯起眼睛,眸光潋滟地瞧了安德一眼,微微点头,与陶常宁手牵手,略过他,慢慢走远。
text-align:center;"
>
read_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