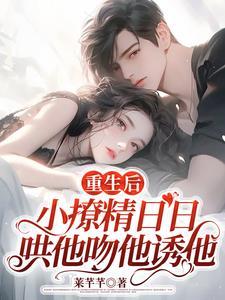69书吧>后悔药多长时间内吃有效 > 第5节(第2页)
第5节(第2页)
☆、第26章
三奶奶看见孙女回来高兴,看见几个孩子冻得小脸通红又笑着嗔怪:“这些孩子,人家老刘家的鱼塘被你们祸害了吧?想吃鱼说一声你刘叔上赶着送,哪用得着自己去捞,看看一个个造的,跟泥猴似的!快进来,普拉普拉身上的雪。”
杜恩恩兴奋的一边脱衣服一边说:“自己捞鱼真好玩,奶奶,这鱼咋做好吃啊?”
李妙一听就乐了:“就知道吃啊,小丫头。”
刘悦得意的说:“我捞上来的最多,三奶奶你看这个还有这条都是我捞上来的!”
三爷爷笑道:“这都是鲤鱼和三道鳞,老刘家的鱼养得肥着呢,那都是我教他的养鱼的方法,你三奶奶的酱炖鱼是绝活,贼好吃,等会让三奶奶给你们炖上。”
晚饭本来是打算包饺子的,现在几个孩子拎着大桶鱼回来,自然是趁着新鲜吃鱼了,三奶奶焖了一大锅米饭,在锅里放上油,放上葱姜蒜爆香,下大酱,加水,水一开就把两条收拾好的鲤鱼扔进去了,为了好吃还放了点小辣椒、八角、花椒和片好的五花肉,等锅开了放进去切成细丝的大白菜、切成块的嫩豆腐,最后放上粉条和香菜。
鱼是用大盆上的桌,大盆里满满当当的,红油油的鱼汤、白玉似的豆腐、青葱碧绿的香菜,散发着浓郁的酱香,一桌人围着大盆热火朝天的开吃。鱼肉香甜多汁、鱼汤鲜美浓厚、豆腐细嫩、粉条滑溜、白菜清爽,几个人吃的简直停不下嘴来。李妙的二叔二婶也来了,还给她们带来了自己家大棚产的水萝卜和生菜。三奶奶看几个孩子吃的开心,也高兴,李二叔和三爷爷各自倒了盅酒,就着蘸酱菜喝的有滋有味。
晚上李妙领着俩孩子住在北面的大火炕上,三奶奶给铺着厚厚的干净褥子,又暖和又舒服。刘悦感慨的说:“老师,我以前看电影总觉得农村生活特别苦,现在我才知道,农村的日子才过的舒服啊,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饭下地干活,多有意思啊!哪像我们家,从来就凑不到一起吃饭,房子倒是大,可冷冷清清的,什么意思都没有。”
杜恩恩也说:“是啊,我爸成天忙,我妈成天盯着我,我觉得我们那个不像是家像冷冰冰的监狱。”
李妙在黑暗中皱皱眉,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其实活的也很可怜啊!剩下的两天假期,刘悦和杜恩恩都玩疯了,刘大奎和柱子都是十一二的孩子,正是精力旺盛恨不能上房揭瓦的年纪,成天变着花样的领着一村的孩子玩,现在来了两个城里的漂亮姐姐,啥也不会玩,还不争先恐后的显能耐?今天带着她们抽尜、明天带着她们打爬犁,还用竹片子自制了滑雪板带着她们从大雪坡往下滑,刘悦和杜恩恩觉得特别刺激,开心的不得了。三天假期过后,李妙带着刘悦和杜恩恩上了刘家司机特意来接得车,刘悦和杜恩恩十分的舍不得,把身上的小零碎都给了李正气几个孩子留作纪念,抱着三奶奶眼泪汪汪的,把老太太弄得心里也挺难受,一个劲的说等考完了学,再来住上一个月。
转眼寒假来临了,对于大学生来说寒假是幸福的蜗居生活,可以什么都不干就在家睡懒觉,李妙计划了一下,准备在家好好复习争取明年英语六级一次过去,趁着假期还得好好给俩学生补课,她们七月份就到考期了,她努力的回忆也没想起来前生中考时的题,那个时候她竟忙着跟丁翰谈恋爱了,好像只记得一道英语作文题,那是她们老师特地拿出来让她们看看,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考了,不管了,哪天让她们做做看,尽人事听天命吧!
李妙幸福的睡了个懒觉,文林老区的供暖非常好,屋子里白天也有23度左右,李妙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走出自己的房间,父母姐姐都上班去了,家里就剩下了她自己,桌子上放着母亲给她留的早饭,小米粥、油条、红油拌的八宝咸菜,简单舒服。李妙吃过早饭,刚坐到桌子前,就听见院子里传来咚咚的声音,这是收废品的,李妙皱皱眉,忽然想起昨天母亲让她今天把家里的旧报纸拿去卖掉,忙推开窗户喊了一声,让收废品的人等等,拎着一麻袋的报纸吃力的下楼。
收废品的是个五十多岁的河南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操着河南腔的普通话告诉李妙报纸现在六毛钱一公斤,拿着一个钩子称称一下,说十一公斤多一点,给你六块五吧!李妙此刻完全没注意到收废品的人给她多少钱,她的全部精神都放在那破烂的三轮车上几轴脏兮兮的画轴上,心里忽然记起前生的一件事来,那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吧,他们文林老区内出了一件大事,B区的一个小买卖人从一个收废品的人那里无意中买了两幅画,当时是想把这画收拾一下当古画出去骗人,或者送个礼什么的,谁知道拿去一鉴定发现竟然是真品,一个收藏家找上门来用五十万收走了,那人一下子成了富人,从小区搬走了,周遭人都说他走了狗屎运了。
李妙对古董一窍不通,但因为母亲唠叨了几次,五十万在01年也是个大数,所以印象比较深,这个卖废品的是不是那个人呢?李妙心里擂鼓似的砰砰的跳,一咬牙:“大哥,这画是你的吗?”
河南大哥不以为意:“哦,是在农村人家当旧报纸卖给我的,咋了,小姑娘你喜欢?”
李妙伸手拿过画展开看看,上面是一副工笔《雨后荷花图》落款是蒋南沙,另一副是一副写意的山水画,上面的落款是檀园(李流芳),李妙看了看都不知道,回头问问老爸吧,也许他能知道,李妙干脆的一指那画问:“大哥,你这画卖吗?”
有生意上门为啥不卖?拉到废品收购站也是卖,看着姑娘的样子文文静静的应该好骗,大哥笑呵呵的说:“卖,我这画是二十块钱收的,你给我二十五就行,两幅五十,中不中?”
☆、第27章
李妙面部抽搐简直不知该哭还是笑,痛快的拿出五十块钱递过去,抱着画就要走连自己那报纸钱都忘了要,大哥拿着钱十分高兴,今天生意真好,哪来的这傻妞啊,忙招呼:“哎,姑娘,你等会,我这还有点东西,你看都是那一家收的,还有一副字,这个这个花瓶子你要不要?”
李妙一震,忙回身看,那大哥从车子底下又翻出来两幅字,一对青花瓷瓶和一方黄色的印章,李妙皱皱眉,心想,如果这都是一家卖的,估计是家里的什么愚人把老辈的珍藏当废品了,可惜啊!
她干脆的问:“这些我都要了,你开个价吧!”
卖废品的刚刚见她皱眉还以为是不乐意呢,见她询价干脆也不废话:“一共一百五,成不成?”
李妙又拿出一百,跟他要了个兜子把东西一装转身就回家了,进门后把门锁死,才摸着胸口砰砰乱跳的心脏,长长的松了口气!展开那两幅字,分别是一副狂草,一副楷书,狂草题的是李白的将进酒,落款是南宫生(宋克),楷书是题的是唐代诗人黄滔的【别友人】“已喜相逢又怨嗟,十年飘泊在京华。大朝多事还停举,故国经荒未有家。鸟带夕阳投远树,人冲腊雪往边沙。梦魂空系□□岸,烟水茫茫芦苇花。”
落款是云中沈民则,李妙一看就愣了,她自幼学习书法,对于南宫生和沈民则都是知道的。这南宫生其实名叫宋克字仲温,一字克温,吴郡长州(今苏州市吴县)人。居南宫里,号南宫生,人称南宫先生。是明代初期闻名于书坛的书法家“三宋二沈”
之一。据《明史·文苑传》谓:“克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
其真书出自钟繇,行草兼二王及皇象《急就草》之遗意,清劲古雅,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将章草融合到他的行草中去,而别开生面,吴宽《匏翁家藏集》评其书谓:“克书出魏晋,深得钟王之法,故笔精墨妙,而风度翩翩可爱。”
可谓中的之语。沈民则名叫沈度(一三五七至一四三四),明代书法家,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擅篆、隶、楷、行等书体,与弟沈粲皆擅长书法,藏于秘府,被称为“馆阁体”
,为明代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书法结体平正,笔致光洁,景色乌黑,风格秀润华美,适合皇家的欣赏口味和审美标准。沈度以长于台阁体书法而深受明成祖朱棣的赏识,被其誉为“我朝的王羲之”
,名重一时。沈度还有一件举世闻名的作品,那就是永乐大钟上的经文。永乐大钟上的23万余字均为沈度所书。再看那对青花瓷瓶,高不过一尺多,丰肩、圆肚、下收,足稍外撇,瓶子口和足都画着栀子花纹,瓶身上画着一副陶渊明赏菊图,两个瓶子的颜色都很亮丽,李妙看了就很喜欢,翻过来一看瓶底,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李妙倒吸了一口冷气,不是吧?这不会是元青花吧?她记得前生她在电视上看过的鉴宝节目里提过,2005年7月,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出1568。8万英镑(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相当于整整两吨黄金!
黄色的印章方方正正的,不知是什么材质的,上面的篆字李妙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来,不过那印章小巧玲珑,温润细腻,对着阳光看时半透明的,能够看到出其中的纹路来,李妙觉得很漂亮,心想要是赝品也不错,起码自己挺喜欢,不行就给自己当个把玩的玩意儿也好。
看着这一大堆的东西,李妙足足楞了一上午,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假的呢也没什么,顶多被骗去150块钱罢了。要是真的,那自己可就发了,呵呵,李妙自己在家傻笑了一天。
晚上李仲文回来第一时间拿给父亲看,李仲文一辈子浸淫在中文当中,虽然不是什么古董鉴赏专家,但对于画画的两位画家却是知道的,蒋南沙本名蒋廷锡(1669年-1732年)江苏常熟人。字扬孙,一字西君,号南沙、西谷、青桐居士,江苏常熟人。雍正年间曾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是清代中期重要的宫廷画家之一。卒后谥文肃。是清代画家。擅长花鸟,以逸笔写生,奇正率工,敷色晕墨,兼有一幅,能自然洽和,风神生动,得恽寿平韵味。点缀坡石,偶作兰竹,亦具雅致。曾画过《塞外花卉》70种,被视为珍宝收藏於宫廷。
那檀园真名李流芳(1575~1629)是明代诗人、书画家。字长蘅,一字茂宰,号檀园、香海、古怀堂、沧庵,晚号慎娱居士、六浮道人。歙县(今属安徽)人,侨居嘉定(今属上海市)。三十二岁中举人,后绝意仕途。诗文多写景酬赠之作,风格清新自然。与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合称“嘉定四先生”
。擅画山水,学吴镇、黄公望,峻爽流畅,为“画中九友”
之一。董其昌赞道:“长蘅以山水擅长,余所服赝乃其写生,又有别趣。”
山水外,李流芳又善作水墨写意花卉。他的花卉,笔势飞舞,泼墨淋漓,别有一种逸趣。归昌世叹为:“其娟美之致,俱在笔墨之外,真不可及。”
董其昌评为:“竹石花卉之类,无所不备。出入宋元,逸气飞动。”
总之,李流芳的高超画艺使他成为晚明画坛上卓有声誉的大家。李流芳还精于治印。他宗法文彭,上溯汉制,又自具创意。是三桥(即文彭)派中骨干,与皖派篆刻大家何震齐名。
☆、第28章
李仲文觉得自己对于古董知之不多,第二天请了一位专门搞古董的朋友来看,这位朋友姓程名叫程远山,祖上就是开古董店的,手上历过的宝贝很多,眼光精准,在北京著名的潘家园有个不小的店面,在古董界很有几分名声。李妙和宁朴见这位程先生穿着件黑色的对襟破棉袄,黑色老头鞋,邋里邋遢,长脸,皮肤微黑,看上去六十多岁,眼睛本就不大,却还总是懒洋洋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李妙是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个古董鉴赏专家,心想老爸这是打哪淘换来的人啊?看他更像个古董!
李妙和宁朴小心的把字画拿出来,徐徐展开,程远山一见字画眼睛霎时睁的老大,放射出的精光简直就像饿狼见了羊群,吓了两人一跳。
他拿出把头凑上去仔细看画,又伸出手捏捏纸张,鼻子还凑上去闻了闻,李妙纳闷啊,这古董字画难道还可以闻出来?她不知道,过去当铺的掌柜各自都有一手绝活来辨别器物真假,这程远山家用的就是鼻子来嗅,从纸张和墨的残留气味中来辨别真假。
半天,程远山直起腰沙哑的开了口:“真迹,都是真迹,老李,这幅蒋南沙的画你卖吗?我出五十万。”
宁朴吓了一跳手一抖差点把画扔到地上去。三口人面面相觑,一副五十万,四幅就是二百万啊!难怪古人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掖草不肥呢!李妙挠了挠头,说:“程老,难不能请你帮我看看,我这还有一对青花瓷瓶和一方印章。”
程远山看见瓷瓶和印章,眼睛越睁越大,精光四射,李妙一家怀疑他会不会把眼珠子瞪出来,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才沉吟到:“丫头,你爸说这些都是你的?”
李妙点点头“你答应我一件事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