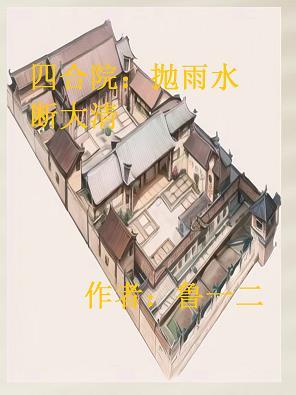69书吧>狠角色的女人特点 > 第4节(第2页)
第4节(第2页)
他们打牌的地方也在园子里,三开间的大屋子,灯火照得屋里屋外通亮。外头是花圃,春花已经尽谢,绿荫在夜里成了浓重的黑影,随风略有摇摆。檐下几口大缸养了睡莲和锦鲤,丫头们凑在缸边拿点心的碎屑逗鱼,听着里面的热闹,偷偷地笑,一边和小月低声细语。
“五少奶奶又来了,做啥都急吼吼。”
“从小当家的不一样,凡事想得早。”
五少奶奶是沈家老太太的远房亲戚,十岁出头没了娘,父亲没续弦,她做大姐的拖着一排弟妹长大。老太太怜她年幼失母,一向多加照拂,又看她是个能干的,到了婚嫁年纪就做主聘了家来做孙媳妇。五少奶奶肚子争气,进门几年连生三个儿子,会挑她刺的也只有小姑了。然而小姑迟早要出门,再说做小姑难免都有两分刁钻,所以对于她们的冷嘲热讽,五少奶奶并不放在心上,笑眯眯地引着小儿子说话,“要不要跟了大娘娘去看大伯伯?我们将来也像大伯伯一样文武双全做大官。”
五少奶奶若无其事,六小姐和八小姐拿她没辙。明芝百爪挠心想知道原委,可这种事哪能由她开口问,问了就成笑话。
一桌子聊天归聊天,手上该打的牌仍在进行着,明芝一冲三家,心痛之余倒有点麻木了。事已至此,她知道与否并无区别,不如把心思放在牌局上,再输下去恐怕今天要大大破财。
友芝饭后和徐仲九散了回步,远远看见客堂那边灯火通明,不由撇嘴,“我最烦打牌,幸好家里没人喜欢这个,就是老太太偶然有了兴致,也不叫我们去陪。”
徐仲九笑道,“亲友聚会枯坐无聊,打牌可以联络感情。”
友芝摇头,却没说什么。徐仲九问,“怎么?三小姐有话不妨直说。”
“你是不是总怕得罪人,喜欢帮别人说话?”
友芝站定了看向徐仲九,“你是县政府的秘书,放着公务不理来陪我们,是不是怕得罪我家?”
友芝和明芝长得都像父亲,个子高,眼睛圆圆的又黑又亮。
徐仲九没避开她的逼视,坦荡荡地说,“我来梅城不是一天两天,县长和令尊的为人更不需我辩说,他们岂是以势逼人之辈。至于我何以愿意效犬马之劳,”
他顿了片刻,对上了友芝审视的目光,“三小姐,你们家和和睦睦,我忍不住就想亲近……”
他态度诚恳,友芝为自己的无礼一羞。不过她不是明芝,虽然脸红得发烫,仍然把想说的话坚持说完,“我不想嫁人,以后我要上海读大学。你不必在我家浪费时间。”
徐仲九点点头,“知道了。”
友芝早有准备要听他一番言语,也准备了一些话以表明自己的决心,没想到如此简单,眨了眨眼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徐仲九又是一笑,“走吧。”
友芝站在原地,“你别告诉我母亲。”
“不会。”
“也别告诉大表哥。”
“不会。”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鲁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