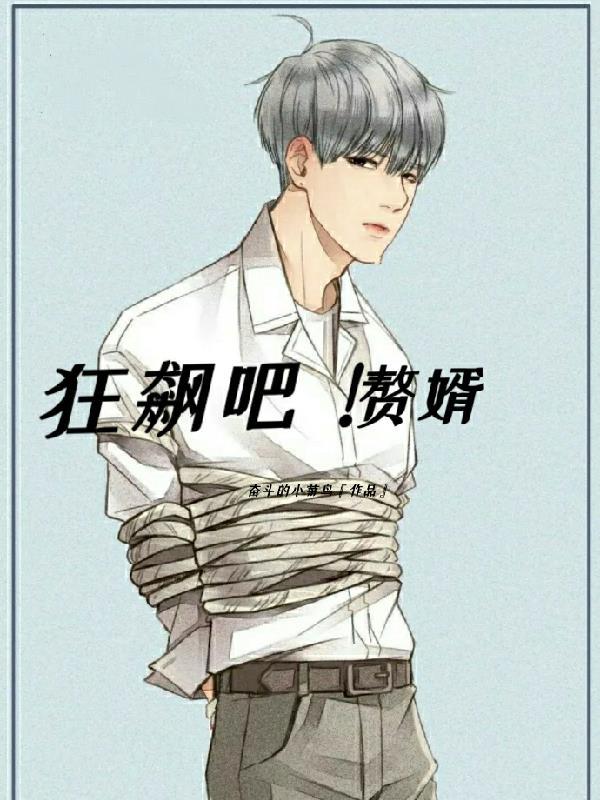69书吧>动机冲突的四种类型举例 > 第27页(第1页)
第27页(第1页)
9点多了,山本起身告辞。走到门口的时候,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对送他的及川先生说:&1dquo;这个,请您转交给静江。出狱 以来攒的,我现在用不着。”
山本终于动了笠井的钱。
及川把一大沓子耖票从信封里拽出来,吃惊地看了山本一眼,默默地数起钱来。
时间过得真慢啊——山本好像要躲避什么似的把视线从及川手上转移到别处去,落在随意扔在鞋架子上的一个大信封上:&1dquo;哈巴罗夫斯克劳改营难友座谈会”。
&1dquo;哈巴罗夫斯克劳改营?不对呀,及川跟我父亲都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劳改营嘛,怎么去参加哈巴罗夫斯克劳改营的座谈会?野崎的那张传单上原关东军一等兵写的文章上,也说及川是哈巴罗夫斯克劳改营的。可是,及川探监的时候分明说过,他是因为跟父亲同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劳改营待过才来看我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dquo;这么多钱,怎么来的?”及川显得有几分惊诧地打断了山本的遐思。
&1dquo;啊&he11ip;&he11ip;那&he11ip;&he11ip;是我出狱以来攒的。”
&1dquo;当然了,你给静江母子多少钱都不能说多,不过话说回来,你刚给了15万,今天又给3o万,静江会怎么想呢?”
我正是为了让她对我有想法才给她这么多钱的——这话山本不能明说,于是他激动地说了下面一番话:&1dquo;请您给她送过去
吧,求求您了!我想尽力为静江做点儿什么,可是除此以外我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啊!”
山本说着说着觉得胸口热得烫。是的,除了给钱以外,其他可以使静江动心的手段一个都没有。赃钱也是钱,顾不上及川
先生怀疑了。只要静江能回头看他一眼,叫他干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
及川不太情愿地把钱收起来,嘱咐山本以后不要太勉强了。山本深深地向及川鞠了一躬,离开了及川家。回家的路上,他心里乱得要命。静江收到这钱以后,反应如何呢?
用了笠井的钱以后,脑海里天天在扩大的静江的笑容就完全消失了。
13
等待也是一件快乐的事。
但是,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还是听不到静江的反应。当然,静江的反应将由及川传达,可是及川根本就没给山本打一个电话。
山本还想到了另外的可能性。比如说,虽然他不知道静江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但静江不一定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如果她知道的话,说不定会直接打电话给他。盼静江的电话盼了好几天。
电话没有盼来,又盼起信来。毕竟已经离婚十多年了嘛,电话恐怕是不会打的。但是,写信总是有可能的吧。信嘛,当然来 不了那么快,收到钱以后总不会立刻提就写的,怎么也得考虑个三五天,比如今天才写,等他收到还得过几天。
转眼又过去了一个星期,山本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
他闷闷不乐起来,被一种半途而废的不祥之感弄得坐立不安。3o万太少了?给4o万就好了,把笠井给的那9o万都给了就好了,那样肯定就有反应了。不对,上次加了五万还表示感谢了呢!3o万不能说少,但为什么&he11ip;&he11ip;
&1dquo;那钱送到静江手上了吗?”怀疑的矛头开始转换方向。及川先生把汇款的事忘了?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把他想得再坏一点,揣了自己的腰包?山本不能跟静江取得联系,无法确认是否收到,难道及川钻这个空子把钱贪污了?及川靠有限的养老金过活,紧紧巴巴的,虽然他有那么多头衔,但有没有报酬啊?3o万哪,对及川能没有吸引力吗?
怀疑到这个份儿上,山本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很卑鄙。及川先生是自己的大恩人,如果没有他帮忙,关于静江的线索连个影子都找不到。
但是&he11ip;&he11ip;
真是什么大恩人吗?关于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及川确实是山本的大恩人。可是,他说他跟山本的父亲一起被关押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实际上是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他为什么要说谎呢?难道就是为了接近我?
山本的疑心越来越重,几天以后,他再也忍不住了,也没打个电话就直接到及川家去了。及川不在,等到很晚也不见回来,报纸上开始在头版头条报道有关竞选市议员的消息,不管出马还是不出马,都得去忙活这个事儿吧?
就在这天晚上,两个多星期以来没有任何消息的笠井来电话了。
&1dquo;山本先生,我实在受不了了,求求您了,求求您答应了我吧!”笠井的声音好像是从水底冒出来的,一种垂死挣扎的声音。他说,刚刚为第二盘录像带交付了2oo万。
以前有过的那种愉悦渐渐充满了山本全身,这些天的烦躁忘了个一干二净。同在地狱里的人境遇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山本
还趴在苦海边上,那笠井就已经掉进苦海了。同样是不想沉人苦海,笠井所受的煎熬要比山本大得多。
笠井说:&1dquo;这回也是在池袋的那个停车场,恐怕下次还是那个停车场。我打算下次实行我的计划。山本先生,您听听我的具
体行动方案好吗?”
一瞬间,山本的心里产生了一个连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的想法:这次给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