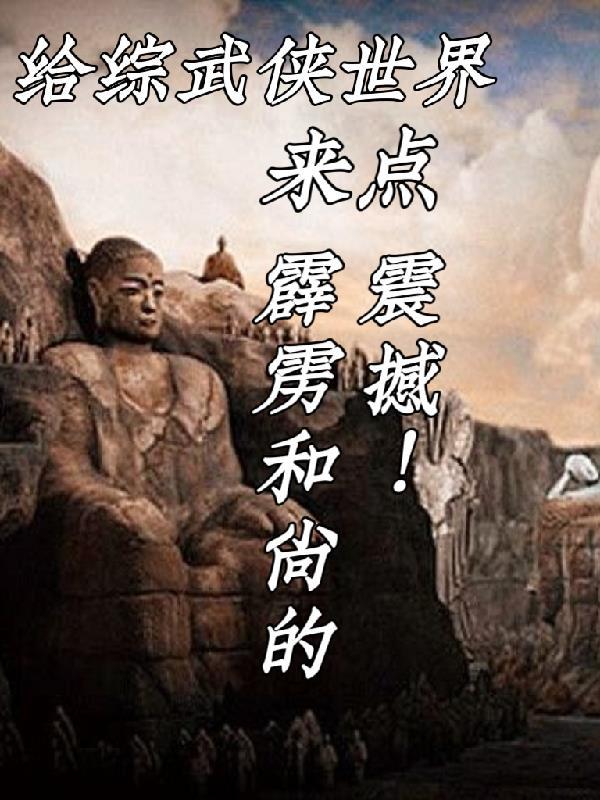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臣尽欢txt书包网 > 第16页(第1页)
第16页(第1页)
府中引活水,建未名池,其上修筑清风游廊,烟波画桥,浩浩渺渺。三个丫头在游廊之中并肩而行,杨柳的步子却在刻意地放缓,阿九侧目微微一瞥,只装作毫无所觉。不消几时,杨柳已经完全走到了她同金玉的后头,她面上一丝不露,手臂微微使力,不着痕迹地将金玉推到了边上。前方一道回转,杨柳瞅准了时机,心中暗暗拿定了主意,面上浮起狰狞之色,卯足了力气朝阿九一扑,欲一不做二不休,将她推落水中。然而令杨柳没有料到的,前方那人似乎早有防备,身子轻轻一侧,不费吹灰之力地闪了开,顺势捉了她的手臂,眸子对上那双惊惶的眼,腕子一转使了个巧劲儿。金玉愣愣的,只听一阵巨大的水浪声在耳畔响起,回过神后廊上早没了杨柳的影儿,人已经落水里了。&ldo;救救我……救命……&rdo;未名池里的杨柳显然不识水性,她面上又惊又恐惶骇交加,扑腾着双手挣扎不休,口里声嘶力竭地呼喊。&ldo;她好像快沉下去了……&rdo;金玉吓得脸色惨白,捂着嘴道:&ldo;怎么办,怎么办……&rdo;溺水的人愈是挣扎,愈是沉得快。阿九冷眼观望神色如常,很快收回目光,扯了已经吓傻的金玉离开,边走边催促,&ldo;不是还得摘玉兰么,有什么好看的。&rdo;金玉声音在发颤,悚然道:&ldo;她或许会淹死的……&rdo;&ldo;她是死是活和你有什么关系。再者说,她再嚷大声点儿,没准儿就有人来救她了呢。&rdo;她面上淡漠而平静,很快拉着金玉穿过游廊绕了一个弯,身后的呼救声愈发地模糊,渐渐便听不见了。直到两个丫头的背影从视野中完全消失,一个身形颀长的男人才从廊柱背后徐徐踱出来。逛个花园儿都能撞上这么一出好戏,果真不虚此行。未名池的水面已经趋于平静,落水的人已经完全沉了进去,连头顶都瞧不见了。他的目光投落上去,沾染上几分惋惜的意味,是时日光从云层后头折射而出,他在太阳下头长身玉立,愈加衬得宝相庄严,悲悯似佛。杨柳的尸体是傍晚时分被捞起来的,身子已经整个儿泡得发胀,眼睛瞪得很大,俨然死不瞑目。在相府,死了一个下人同死了一只鸡鸭没什么区别,加上府中有客人拜谒,更是不能声张。杨柳的死没掀起任何风浪,姚总管看见尸首时掩面骂了声晦气,接着便打发人将尸体拿破席子裹了,匆匆扔去了城郊的乱葬岗。同阿九预想的一样,在这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地方,死了一个婢女,不会有任何人追究,也没有任何人介怀。倒是为难了金玉,她胆小如鼠,自然不比阿九淡定如常。听说杨柳真的淹死了,吓得躲进被窝直打哆嗦,口里颤颤道:&ldo;她死了,会不会回来找我报仇……&rdo;阿九叹了口气,走过去安慰她,道:&ldo;人是我推下去的,要报仇也是回来找我。&rdo;金玉还是很害怕,裹紧了被子语无伦次道:&ldo;我见死不救,是我见死不救,如果我救了她,她就不会死,她就不会淹死了……&rdo;说着忽然一顿,眸子瞪得大大的,死死看着她:&ldo;你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怎么能对人命如此冷漠?她虽然可恶,可罪不至死!&rdo;&ldo;……&rdo;阿九有些无可奈何,她没有想过要置杨柳于死地,可金玉这副模样,似乎也没有解释的必要了。她心头嗟叹,洗漱毕后便除了衣裳上了床榻。褥子是冰凉的,睡了好一会儿也没觉得暖。她翻了个身面朝着外头侧卧,见金玉仍然在瑟瑟发抖,便移开眼,眸子望向窗外。今夜是上弦月,如弯刀一镰悬在天际,似咫尺,却又遥遥不可及。不知过了多久,那头的金玉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微微发颤,道:&ldo;……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事……&rdo;她面上却仍旧淡然,唇角勾起个淡淡的笑,道:&ldo;你没有对不起我。&rdo;其实无怪乎金玉会是这样的反应。安乐长大的姑娘,怎么会理解一个深渊里的人。☆、陌上鸢冷,好冷。寒气从身体的某处弥漫上来,一丝一缕爬遍四肢百骸。这滋味难受得无以言表,像是身体的各处被无形的利刃捅了大大小小的窟窿,有腊月的冷风从这千疮百孔的躯壳里钻进来,像凌厉的刀子一下下割破了皮肉,冷彻心扉,翻搅着五脏六腑,使人痛不欲生。迷茫的白雾萦绕在眼前,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真切。身子像被浸泡在化了冰的河水中,她在昏迷中无意识地抱紧了双臂,娇小孱弱的身子在软榻上瑟缩成小小的一团,眉头紧皱,苍白的双唇细微地颤抖,神色极是痛苦。这回不是错觉,她能极其清晰地感觉得到,那只蛊虫正在自己的血肉里游走。它缓慢地挪移,所经的每一处都掀起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和寒冷。从前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这回却前所未有的强烈,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将身体抱得更紧,咬紧了牙关承受着一切。迷蒙中,脸上传来一丝异样的触感,似乎有人用指尖抚过她的颊。她紧锁的眉头皱得更深,偏头去躲,却怎么也摆脱不得。那人简直不厌其烦,带着暖意的指尖滑过她光洁的左颊,慢条斯理地来回抚摩,轻盈的,酥麻微痒。未时许,夜色已经极深。穹窿漆黑一片,如泼上了浓墨,玉蟾被整个儿掩盖在簇簇乌云之后,透不出半丝光亮。晚间的风透着几丝凉意,地上的几片青绿的叶被打着旋儿吹起来,从洞开的窗扉送入,轻飘飘地落进来。屋子里燃了夜烛,入夜时分点起,此时蜡炬只剩下短短的一小截,火光被风吹得飘摇,呈现几分寂寥将熄的意态。谢景臣坐在床沿上,迟重的金辉照亮他的半张脸,浓长的眼睫投下一圈淡淡的阴影,轮廓被勾画出几分温暖的韵味。视线微侧,瞥见落在肩头的落叶,因伸手轻轻拂落,目光重新回到榻上的女人身上。她脸上蒙着一层淡淡的冰霜,眉头深锁浑身发抖,显然正承受着极大的痛苦。金蝎蛊在体内,一旦蛊毒发作,即便是身强力壮的男人也难以忍受,由此可见,她确实是个意志力极其顽强的女人。一个人对生存的渴望究竟要强烈到什么地步,才能熬过每一次的毒发,熬过每一次如炼狱一般的痛苦。他面无表情,修长如玉的指尖拂过她拧起的眉宇,抚上尖俏的下颔,却并没有收手的打算,势头一路往下,滑过纤细的脖颈,精致的锁骨,动作缓慢而优雅,最终在急剧起伏的胸口处停了下来。确定身体没有丝毫的不适同排斥后,谢景臣徐徐将手收了回来,面上仍旧淡漠而平静。他厌恶与人接近,这是幼年练蛊时落下的病根,天下间无药可救,久而久之也便习惯了孤独。如今,这个女人倒成了个意外。谢景臣唇畔勾起一个寡淡的笑,眸光一瞥,不经意地落在那光裸的肌理上。薄霜覆了淡淡的一层,在火光的映衬下被镀上凝金色,傲人的双峰间沟壑极深,在轻薄的衣裳下若隐若现,看上去神圣而撩人。体内那股莫名的欲望又开始升腾,勾惹着下腹的蠢蠢欲动。他眸色一深,意识到了不身体的异样后很快移开了目光,接着便仿佛一刻也不愿多留了,起身拉开那扇有些破旧的木门,大步踱了出去。风吹树摇,枝叶于喁,他在夜风中施施然而行,一路分柳拂花,招惹上一身芬芳。身上的单衣有宽大的琵琶袖,在风中翻飞,猎猎作响,那双清漠的眼半眯起,目光落在远处夜色中起伏的山脉上。一个常年身处高位,习惯了操控天下的人,不能允许世上出现任何一个意外。他的当务之急,恐怕是控制好自己对阿九那股由于金蝎蛊而滋生的欲念。古语有云:清明断雪。倒春寒一送,日子便彻底好过起来。辰时许,视朝方毕,闻得一公鸭嗓儿吊了声儿&ldo;退朝&rdo;,满朝的臣工因从太和殿里头依次而出,走在最前头的那人一身行蟒官服,风姿绰约,眉目如画。谢景臣面上挂着副不咸不淡的笑容,微侧着首,似乎正与身旁的一个官员说着什么。众人经过时侧目一看,见认出是吏部侍郎尹尚尹大人。他满面堆笑,朝谢相揖手,殷切道:&ldo;相爷吩咐的事下官都已经办妥,已将余穆二人的余党一网打尽。&rdo;他唇角漫开一个优雅的弧度,&ldo;尹大人替陛下分忧,一片赤诚,天地可鉴。来日,本相定会在圣上面前……好好替大人表忠心。&rdo;听了这话,尹尚心头悄然大喜。在如今的大凉朝,天子跟前儿最红的人便是谢相,皇帝对他信任有加,有他替自己美言,将来何愁不加官进爵,飞黄腾达呢!他眼中浮起几丝热切,面上却刻意摆出了刚正之色,拱了双手朝他揖下去,道:&ldo;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这都是下官分内之事,相爷言重了。&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