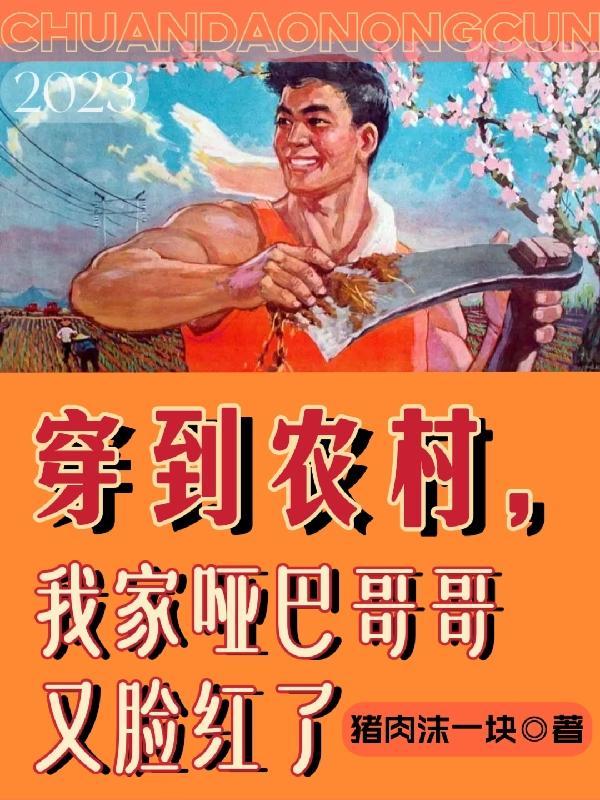69书吧>珠喉的意思 > 第35页(第2页)
第35页(第2页)
沈慈珠起身往卧室走去。
他知道,父亲会给自己实权了,实权比其他一切都更具魅力,沈慈珠必须得到。
第二天晚上,沈慈珠便收到父亲将谢咽调去美国参加分公司会议的消息。
他未言一语,还是父亲主动开的口,晚餐时父亲说谢咽为沈家鞠躬尽瘁十年,也该给他实权了。
“你会难过吗?还会和十几岁时一样……谢咽一离开家里哪怕只是出去给你买个布娃娃,只要你一找不到他,你就会哭鼻子吗?”
父亲微微眯眼,“还会让谢咽把你抱在怀里一遍一遍地哄吗?”
“怎么会呢?那太丢人了,如您所言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小孩子了,父亲,您做的总是对的,再者谢咽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您才是他的雇主。”
沈慈珠放下刀叉,隔着长桌看向父亲,“您的命令高于一切。”
桌上珍馐美馔,沈慈珠有点反胃了。
此时此刻,越海彼岸,美国华盛顿。
会议上谢咽坐在最高位,沉默的视线扫过这些兢兢业业向他汇报公司资料的员工,有个红裙金女郎对他遥遥眨眼,似在邀约。
谢咽移开目光,会议结束后他回了别墅。
沈慈珠方才在会议上就给他打了电话,他没有接,因为会议全程都在被沈家主监控,为的就是杜绝两人的死灰复燃。
沈慈珠自然也是知道的,他打电话,只是为了让谢咽难堪而已。
谢咽一边对不起自己的救命恩人,一边对不起自己的前任伴侣。
谢咽独自一人时他喜欢光亮,窗帘大开他坐在床边,解着西装领带,衬衫下的男性躯体健硕高大,像一座内敛又危险的山,他的脖子上有道横了一圈的疤痕,当年被割伤时,仿佛深可见骨。
这里的时间与国内全然不同,时差之下,他静静等着沈慈珠给他第二遍打电话,孤独又不安,像一条害怕被主人丢弃的大狗。
他的手机旁人都是默认铃声,只有沈慈珠的是震动,是无声下也汹涌的震动。
震动响起,他滑动接通,琥珀色的眼看着别墅外美国的高楼大厦,车水马与中国太远了。
“你……还好吗?”
谢咽说着,他察觉到了什么,于是担忧道,“是不是又喝酒了?你的身体不好,可以不要喝了吗?”
沈慈珠如他所料喝了酒,晚餐后自己在卧室毫无节制地饮酒。
“Qu’est-cequetufous?你人呢?”
沈慈珠的语调低热,法语中文颠倒混乱,隔着手机,谢咽甚至听见了酒入喉和酒在瓶子里晃荡的声音。
“谢咽,酒没了,给我拿一瓶过来好不好?不要告诉父亲……我只喝……这一回。”
沈慈珠好像抱着酒瓶子在床上倒下了。
不知道有没有穿好衣服,别又只是穿一件白衬衫就醉酒睡了,那会烧的。
沈慈珠非常容易生病,又不喜欢吃药,每次吃药都要谢咽百般哄着,实在不行得用打针威胁,沈慈珠才愿意咽下去。
“乖,等我回国,好不好?”
谢咽的手背满是青筋,落地窗外日光明明灭灭,他的面部轮廓没了外人眼里的狠戾,看上去温柔极了,“我很快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