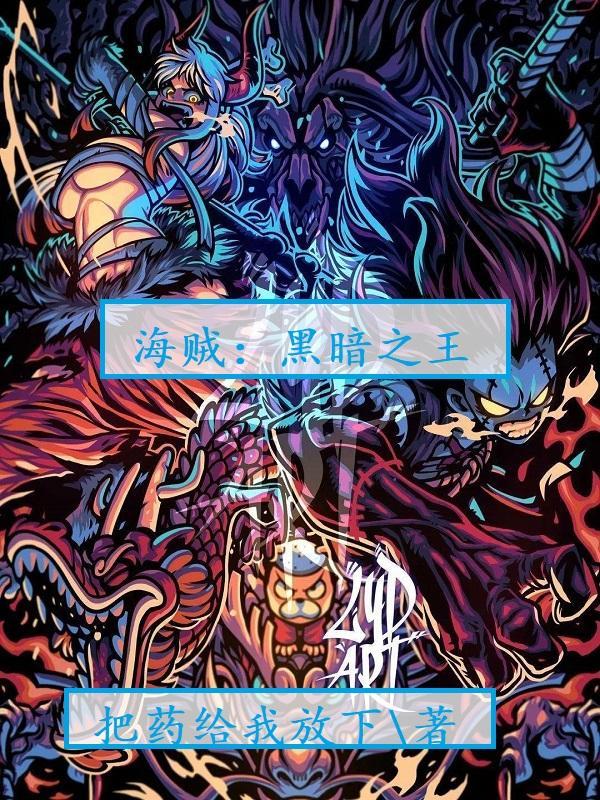69书吧>风行云知道番外 > 第3页(第1页)
第3页(第1页)
外面已暗,屋子里更暗。我强烈的感觉屋子里没有人……要不然这么暗的夜晚,为什么屋里不掌灯?但我不敢也不能离开……这就是一个奴才的命运,自由,掌控在别人手中。我的命根硬,这是我的认知。我的亲人在饥荒、瘟疫中一个一个死去,只有我一个安然无恙活了下来。我成为孤儿衣不里体、三餐不继地四处流浪,到最后我以为我会在一次暴乱中死去时,我被训人馆里的人所救并收养。现在,我的这个认知再次被感召。我就这样忍住饥饿站在屋外一天一夜,除了身体因受冻而僵硬了些之外,我没有感到任何不适。黎明破晓前,我眼前一直紧闭的大门被人由里面打开了。走出来的人正是我昨天误以为是天神的人,我现在的主子,冉云蔚。他仍是一身的白衣,提着闪耀锋芒的剑看也不看站在门外的我一眼,径直走向他昨天练剑的地方,那个桃花相依的庭院。他走过我身边时,我本想唤他却才发现我的喉咙已经被彻夜的寒气熏哑了,发不出声。他走过我的身边,无声息地带起阵阵微风。我的心因为他带起的风而激荡着。他越过我后我瞄了一眼大门敞开的屋子。屋子里的装饰跟庭院外的相和谐,同样的,朴实无华。虽然我没有能看尽屋子里的构造但我已经能肯定,这个屋子并没有通向其他地方的门道……那就是说我的主子他真的就这样不吃不喝不吭一声地待在屋子里整整一天?主子他,真的是个怪人呢?望着不远处已经开始舞剑的他,我心不在焉地想着。他练剑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当他收起剑目不斜视向我走来时,我还在为他天姿般轻盈的动作而震撼。直到他回到屋子把门又关上肘,我才惊醒。难道……他又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天吗?不知道是为他还是为也跟着一天不吃喝的我……但当我却要走到门前敲门时,仅移动了脚的我,倏忽跪倒在地。我的脚刺骨的痛,原来,我不止声音被冻哑,连脚都冻到僵硬。脚上传来那被无数只虫子穿刺般的痛,连痛呼都发不出来的我直冒冷汗。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最后却连跪都跪不了。因为痛苦下巴僵住的我的嘴巴里牙齿不受控制地啃伤我的口腔。虽然痛苦,但我却不曾为自己担忧。成为孤儿流浪的时候,我受过比这个更严重的冻伤,当初我都能顽强地活下来,我不信就这样的冻伤能拿我怎么办。既然现在的我站不起来,我只能尽量把身子缩成一团,以便取暖化冻我就这样倒在地上,挣扎着缩紧身子。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昏过去的,但当我张开眼睛时,我发现躺在原地的我的身体上盖着一张不是很厚的毛毯。这张毛毯是纯白色的,这让我轻易地就联想到了我的主子‐‐那个身着白衣的神仙。这张毛毯不是很厚,但却为我挡住了冷风,让我的身子暖和,这样的毡子一定报珍贵吧……我心想着慢慢地坐起身。身子已经不是那么的难受,只是站起来时身体有些痛。此时天已暗下,我没想到我一昏,就昏了一天。这也倒好,不用忍受饥饿的困扰。好不容易站起来的我刚这么想,就听到肚子在抗议。可现在的我没有心情去理会我的肚子‐‐抱着纯白的毯子站起来的我看到了屋子里亮着灯。我抱着暖和的毛毯一阵踌躇,最后,伸手在门上敲了敲。屋里亮着灯,代表此时屋里有人吧?「进来。」我敲门的声音刚落下屋子里就传来了冷漠却柔和悦耳的声音。没对会有人回答我这件事抱有多大希望的我着实呆掉了好久。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我把手小心地放在门上,稍稍一使力,就把原本紧闭的大门推开了。当门开启我看到那个神人般的人坐在正对大门的桌子上看书,推门的声音没有影响到他,他依然静坐在桌子旁没有移动分毫。我站在门外不敢进去,而他的声音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再次响了起来。「有事吗?」他是视线也不抬一下地问这句话的。听着他没有情感的话语,我静了静紊乱的心,才抬脚慢慢地步入屋子。屋子里飘荡着一股淡淡的暖香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就快要走到一直维持原样的他的身边时,我停下脚步伸手把手中的毯子举向前。我这么做是在告诉他,我想还毯子还给他。空气在无言中变得凝重,我跟他就这样维持原状片刻后,是他先有了动作。主子把目光慢慢地移向我,他被烛光照耀的黑眸深邃而幽远,让看他的我有种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的情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