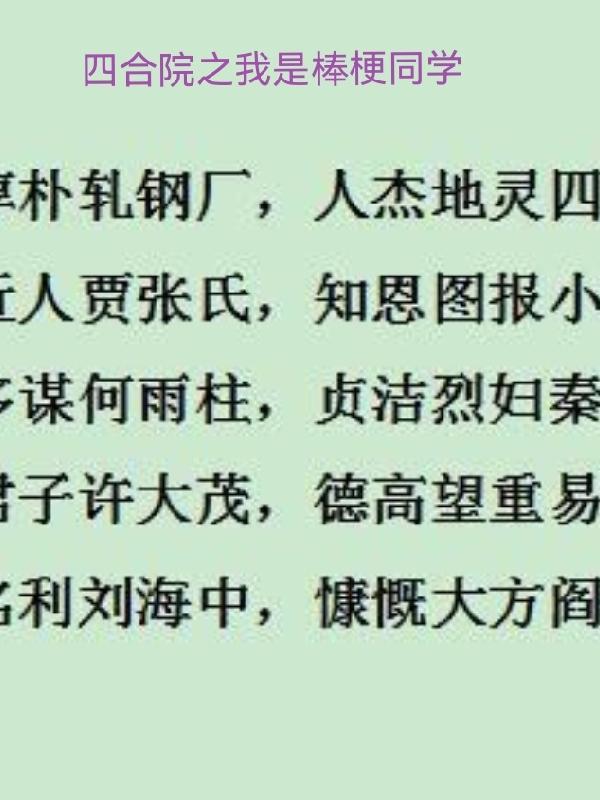69书吧>似匀深浅妆 春风助肠断 > 第三十四章 围城之城五(第1页)
第三十四章 围城之城五(第1页)
在最后一片叶子落地的时候,四周静谧无声,即便是树上喈喈乱叫的虫鸣,也静默无声了。
陶芷感觉天地安静得就像只有自己和那个中年男子。
一切归位平静就好像什么也没有生一样,中年男子却没有半点想逃走的样子,而是在矗立如山一般,挺直了腰干儿,一双目瞳炯炯有神,耳听八方,就好像每一个微小的动静,那中年男子都能感觉的到一样。
就连陶芷也屏息气凝,生怕无端端地招来无望之灾,白白送了生命,何况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
陶芷躲在草丛中,顺着缝隙中望去,只见中年男子鬓凌乱,耳朵微动,突然间中年男子一声大吼:“就是这里。”
树枝微微晃动,倏尔一个黑衣人从树梢一跃而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将手中的似巨大称砣一样的物件抛了出来,那似称砣的东西的一端还连着铁链,铁链碰撞,铮然作响,那人的动作快如闪电,陶芷根本就看不清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那秤砣似的物件,直冲中年男子而去,只见中年男子拍马而起,伴随着一声惊呼:“血滴子!”
中年男子还是行动敏捷,躲过血滴子,可是马没有觉危险,血滴子将马头包裹,只听到一声脆响,有骨头断裂的声音,马还没来得及哀叫一声,已经一命呜呼了,大量的血从马的颈脖之处喷涌而出。
陶芷被这血腥味道,弄的恶心连连,又奈何他们没有离去,又不好作。
豁然间从树梢上接连不断地有黑衣人下来,落地无声,团团把中年男子包围,密不透风。
空气中紧张得似箭在弦上,一触即,其中一个黑衣人说道:“交出烽火令,饶你不死。”
那声音嘶哑异常,犹如破风箱出的声音。
中年男子一声冷哼道:“只怕我交出了烽火令,你们要杀人灭口吧!”
那黑衣人不怒反笑道:“还真不愧是南番王赏识的尚青衣。”
黑衣人的双眸徒然一冷,所有的黑衣人将豁然间齐齐抬手,各自从袖口里出现一条乌黑亮的铁链,铁链由四面八方抛向空中,只听到铁链琳琅如珠的撞击声,铁链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搭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网,那幅巨大的网,从空中而落,将中年男子捆绑,中年男子就像网中的鱼一样,不能动弹分毫。
只见黑衣人齐齐向后退了一步,手中的铁链力道也加紧了力道,任凭中年男子如何挣扎,逃出这个网,这个固若金汤的网也一尘不变。
突然从上空落下一个黑衣人,手持长剑,剑指中年男子的头颅,眼看锋芒逼近,千钧一之刻,中年男子一声大吼,突然气力大得如牛,中年男子将所有的铁链抓住,来势汹汹,也太过突然,黑衣人们始料未及,随着中年男子地低吼声,中年男子双臂只暴青筋,将对面所有的黑衣人都凌空抬起,所有的黑衣人都像脱了线的风筝,随风旋转,只听中年男子的女吼声越来越大,大如洪钟,声如雷霆。
即便是躲在草丛中的陶芷都无法忍受,心潮蓦然得波涛汹涌,像是万马奔驰一样,莫名其妙的忐忑不安。
而离中年男子近的黑衣人们,个个口鼻冒出鲜血,只见中年男子一撒手,那些黑衣人犹如脱缰之马,随着冲劲儿向着四方而去。
其中一个黑衣人落在陶芷不远处,陶芷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那黑衣人已经口鼻鲜血淋漓,好不狰狞。
马已经死了,中年男子似乎有什么急事,正要轻功而去,突然他止住脚步,只见他耳朵微动,目光犀利地看向了陶芷的方向。
陶芷虽然敛神收气,可是心跳犹如雷动,毫不间停。
她知道那人已经现自己。
中年男子的脚步选来选逼近,只到了草丛边,这时突然从中年男子来时的道路转来马蹄声。
由于分神和刚才的打斗,已经耗费了中年男子大量的精力和力气,所以也没有现在的敏捷,中年男子还没有躲入,隐藏起来。
一个声音传入耳中。
“尚大人勿走,是小生付息。”
只见一个面若冠玉的少年,踏马而来。
付息下了马向尚青衣供了供手又重复道:“小生付息,听闻南番王爷在江淮遇害,皇上特地派人相救,奈何途中遇见无数的黑衣人,小生与队伍失散,实在是巧合之极!小生在途中听到尚大人的消息,所以一路打听而来。”
尚青衣眼中的警惕梢减少,言语也温和了许多,说道:“南番王已经被困在江淮,我也是途中听南番王的吩咐,与他分道扬镳,而且我在途中不断有人追杀。”
老南番王已经生老病死,由世子上任为一代的南番王,可是驻站边疆十万大军的战士们没有看见过世子的相貌,那么就以烽火令为号令,也就是说得了烽火令就是得了边疆的十万大军,又因为废太子玄德,起兵造反,好皇帝的江山本来就是满目苍夷,动荡飘摇,所以人心不定,各个诸侯国也各自蠢蠢欲动,无不觊觎南番王的烽火令。
付息一蹙眉,问道:“尚大人可觉是哪路人?皇后的余孽未除,莫不是皇后的人?”
尚青衣摇头道:“不可能,即便皇上宅心仁厚,留下了皇后的一些族人,但为了以妨皇后一族死灰复燃,所以留下的活口也只是一些老弱病残,他们不足一提。但是各个诸侯国和废太一玄德,他们才是大祸患。”
付息赞同的点了点头,又道:“尚大人手持烽火令,得必须尽快赶到帝都,不然就要大祸临头了。”
尚青衣目中寒光一闪,手中大刀毫不迟疑地砍向付息,好在付息身法敏捷,行动快,一个脚尖一转,将大刀躲避而过,付息不解地急急问道:“尚大人你……为何如此?”
尚青衣一身冷笑:“我何时告诉你烽火令为我的手里?知道烽火令在我的手里的人只有那天在客栈杀害南番王的人,只有那天在客栈的人,才看见南番王把烽火令交到我的手中。所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付息大笑道:“看来是一时疏忽大意了,尚大人,你若是乖乖交出烽火令,不仅能免去你的死罪,太子一定还会重重有赏。”
尚青衣骂道:“叛徒,走狗!”
付息没有气恼,而是温和的说:“尚大人,你这话可说的不对,太子可是皇帝之子,也是一脉之血,本公子投靠太子又何来的叛徒之说,况且老皇帝老眼昏花,这江山不是难民暴动,就是贪官污吏,江山本来如雨摇曳,何不让年轻气盛的太子去把持,江山易改,这江山早就有人觊觎,指不定有人盼望着老皇帝薨去,又起兵而反的,何不把江山托付到自己的孩子手中,也免得落入别人的手中改朝换代的好,你说不是么?”
尚青衣听后,面色铁青,怒道:“真是一派胡言。”
付息面色一沉,方才的温和与笑意消失殆尽,脸色犹如腊月寒冬一般,冷的煞人,说:“尚青衣,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付息说完抬起手,摸上腰上软剑,软件铮然而出,剑锋凌厉,直直逼向尚青衣,尚青衣抬手反手一挡,只看见刀剑相见的锋刃,摩擦出激烈的火花。
付息脚尖一点凌空而起,辗转到了尚青衣的身后,在尚青衣的背后又是一个猛击而去,付息说道:“尚青衣拿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