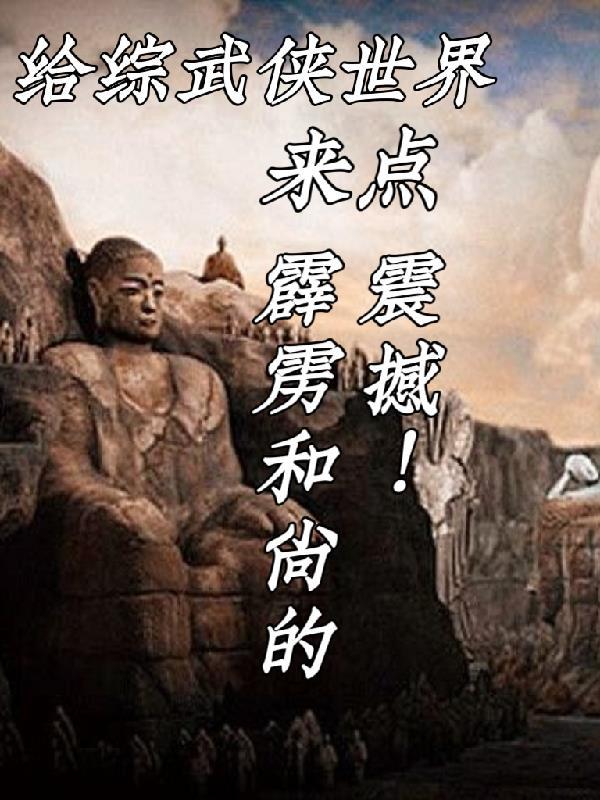69书吧>蜘蛛 > 第50页(第1页)
第50页(第1页)
他的左臂裹着厚厚的石膏,虽然已经打了止痛药,可里面那两根强制拼接在一起的断骨仍然阵阵抽痛。
不过杰森现在没空关注这个,他的注意力全在床边的那个男人身上--沃伦正动作优雅地把一束清丽淡雅的银星马蹄莲插进花瓶里。他有点紧张与厌恶地看着那束花,好像那直挺挺的花梗是一条条昂首待命的毒蛇。
“我不喜欢马蹄莲,拜托换一种吧,剑兰、郁金香或者百合,随便什么都可以。”
杰森无精打采地说。
沃伦最后调整了一下花叶的位置,转身回到床边,“当然可以。不过,浓郁的花香味对病人不好,我想你会改变主意的,对吗?”
杰森郁闷地发现,自己只能回答“是”
,因为对方的问句里没有丝毫征询的意思。世界上总有这么一类人,他们的意见永远是不可转圜的,毫无疑问对面的男人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想了想,决定换个话题:“西蒙怎么样了?我记得他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沃伦微微皱了一下眉,看上去有点不太高兴,但还是用尽量平和的语气问答道:“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就不要多考虑了。”
“你说‘无关紧要’?什么事重要什么事不重要,这是谁划分的?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想我有足够的权利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别这么任性杰森,你现在就像个乱发脾气的小孩子。这么做完全是为你好,就算你现在不理解,也得先接受了再说。”
“为我好?哈,得了吧,我早就年满十八岁而且不姓兰格,这种话还是对你儿子去说比较合适!”
沃伦的脸色沉了下来。怒气开始在他的心底堆积,但他的嗓音却压得更轻更低,仿佛正刻意为情绪的秤杆加上名为“耐心”
的砝码,好让危险的一端别猛然间高高翘起。
“别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杰森,我是在保护你!丢掉那些不知好歹的抵触情绪,否则我保证你马上就会后悔的。”
“‘保护我’?可你还没有问过我需不需要保护!”
杰森习惯性地抬起左臂--疼得抽了口冷气之后,改用右手不耐烦地耙了耙前额的头发,“如果你现在问的话,我会肯定地告诉你:‘不!’我很感激你的出手相救,对此你可以要求报答,但不是用这种方式。或许其他人愿意满足你的控制欲,但我没有义务和兴趣陪你玩命令与服从的游戏,哪怕你在花瓶里插满金条也没门!好了,放我走吧,沃伦,各自去做自己的事。”
杰森一口气说完,直视着床边的银发男人等待他的反应,可惜对方并没有给他多少观察和想像的空间--沃伦的脸色如同一潭深涧,平静得令他无从揣测。
他朝杰森伸出手来,后者下意识地朝后瑟缩了一下。刚才揉乱的金发被沃伦一缕缕拨回原位,动作轻柔得像小女孩对待心爱的玩偶,然后他的手缓缓向下,滑过衬衫半敞的胸口,探进被单握住了右边脚踝,骤然用力攥紧!
杰森险些叫出声来--对方的手劲大得惊人,他的脚踝感受到重力挤压的疼痛,如同被塞进一台不断收缩的锻压冲床,几乎能听见骨节咯咯作响的声音。他本能地挣扎着想要摆脱,却发现对方越抓越紧,这已经不是恶作剧或是威胁的范畴了,那一瞬间他感觉对方是真想把他的脚踝拗断似的下了全力!
“……松手!你发什么神经!这是我的腿,不是他妈的电子握力计!”
杰森愤怒地叫道,一个标准的右侧身借力,随之屈起左腿朝他的手腕狠狠蹬去。
沃伦在挨上这有力的一脚前收回了手,“很疼吗?大概吧,我的握力超过180磅。但还远远比不上骨折的疼痛不是吗。身体健康是一件多么令人珍惜的事,我只是希望你能体会到这一点。”
“哈,这话由一个在病床上躺了半年的‘植物人’来说,确实挺有说服力。但你好像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是谁把我折腾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你自己。”
沃伦严肃地回答,“如果你能听从我的意见,就什么坏事也不会发生。”
“sh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