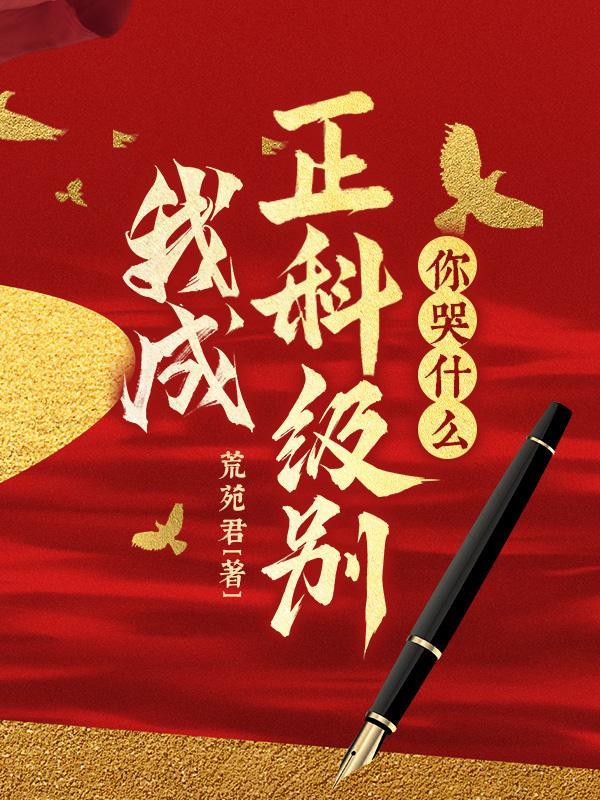69书吧>风往北吹什么时候发行 > 第二十五章(第1页)
第二十五章(第1页)
男娃一直在为这事纠结“打小一直在爹娘的精心呵护下长大,娶了婆姨,有兰子这个贴心人照顾,生活一直很安生。平日里尽干些有兴趣干的念书之类的小事儿,跟家里需要干的生意买卖上的事儿。往常都是跟着别人干,没独自出过远门,也没做过什么太出格的事儿。虽说在镇北也干了两桩跟革命有关的事儿,可有一大帮朋友兄弟谋划打头阵,我就是个打酱油跑腿的。现在要离家独行,跟着一大帮人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干革命,心里还真有些忐忑不安。扪心自问,好象心里既有愧疚不舍,也有壮志豪情,抛家弃子可是需要咬牙狠的。”
海涛看出了男娃的纠结,耐心地跟他讲时局,讲追寻革命的想法,讲家国情怀,也叫男娃看清自个儿的内心,在这个时候不要进退两难、犹豫不决“男人吗,无论对错,干什么就要一鼓作气,认定了就去做。想得太多,什么也就做不成了。”
男娃心里一直很不安,觉得对不起婆姨。从下决心要去上海那一刻起,他就不咋敢看婆姨的眼睛。瞅着婆姨已经开始显怀的肚子,他就心里一阵酸“婆姨肚子里的可是我的娃娃。”
他尽力掩饰着情绪,可婆姨似乎还是感觉到了点儿什么,看他的眼神,拉话的语气,都有一丝异样。也许是男娃自个儿心虚吧,他吃着婆姨做好端上桌的镇北风味饭菜,不时偷瞄一眼婆姨出去进来行动明显迟缓的身子,鼻子就有些酸,眼泪都差点儿滴到饭碗里。他强忍着内心的酸楚吃完饭,就脱了外衣上床躺着,也没心思念书。婆姨问他咋了,他就说“白天跑多了,有些累,早点睡吧。”
婆姨拾掇完家什,回屋瞅见他睡着了,就关了顶灯,在台灯下念书。女人显然也没了心思,没念多大会儿,就上床睡下了。男娃睡不着,又不敢动,硬挺着不吭声,一动也不动。婆姨把被子搭过来,用手抱着他,他也不敢动,任由婆姨摸索着他的身子,心里跟猫抓一样。好不容易,婆姨睡着了,他才敢把身子翻过来,抱住婆姨。放松下来,他心里安生许多,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在梦里,他好像回到了镇北,跟婆姨在大草原上骑在马背上,婆姨在他的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马飞奔向前,他的身子上下起伏一动一动的。睁眼一看,婆姨已经起床做好了早饭,正拍打着他的身子“快起床,吃完赶紧去学堂,要迟到了,睡得这么死。”
男娃赶紧起床洗漱吃饭,着急忙慌背着书包出了门。
男娃想了好几天,时常半夜醒来,听着身边婆姨的呼吸声,一阵阵不舍,几次摸着婆姨的脸,抓着婆姨的手不想放开。男娃确实是难以抉择,年纪轻轻的他其实还是个娃娃,青春的热血叫他难以平复闯荡的冲动,爹娘妻儿又叫他难以割舍。男娃这时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舍得,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有得必有舍。”
在十五六的年岁,就要抛家舍业断舍离,确实有些为难这个小娃娃了。男娃终于还是想清楚了一点“瞻前顾后,甚事也别做,混吃等死算了。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混吃等死也是一种奢望。为了寻求心灵的安宁,还是去大干一场,放任一次再说吧。”
他写了小诗夹在常看的书里“国难当头意难平,拍案而起舍安宁,投身革命浑不怕,一腔热血向南行。”
他希望婆姨翻阅的时候能够看到,谅解自个儿的不告而别。
该来的还是来了。女人好像事先有点儿感觉,可又什么也抓不住。那一天,男娃回来的很晚,回来也不睡,呆呆的在床上躺了半夜,不说话,女人问他话也一声不吭。迷迷糊糊的,女人就睡着了。天一亮,女人就醒了,醒来现男娃已经走了。起初女人也没在意,照样做饭、洗衣,打扫屋子。可这个晚上,男娃没有回来。“以往没生过这种事儿,不管多晚,林子总会回来啊。”
女人心里隐约有种不安的感觉,总觉得有甚事要生,觉也没睡踏实,半夜醒了好几次,竖起耳朵听外面有甚动静,凝神听了半会儿“甚动静也没。”
第二天天一亮,女人就着急忙慌把强子叫到跟前说“林子昨晚上没回来,咋办呀。”
强子一听也着了急,叫了几个铺子里的伙计出去找人。他找了一天,学堂、戏院,男娃常去的地方都打问了,还是没找到“没有人知道少掌柜去了哪里,急死人了。”
女人翻箱倒柜,胡乱翻找,最后在正看的那本书里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我去革命了,革命成功,我就回来。”
女人的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这个尿炕娃竟然撂下人家,一个人跑了。”
女人一阵昏,倒在床上,半天没回过神,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眼前一片黑暗“林子,你咋就这么走了,撂下我可咋办呀。”
男娃背着包袱、挎着书包,跟几个学生模样的男娃娃一起快步出了天津城。回望着远处隐隐约约的高楼,他心里一阵黯然“兰子,我走了,终有一天,我会回来找你的。不是不想带着你一搭去,是你如今身子不方便。原谅我吧,我的好婆姨。”
男娃跟同伴走进一个车马大店,雇了两辆马车,说要去塘沽。谈好价钱,几人放好行李,一个接着一个相帮着上了车。马车开动,众人反而一声不吭,有个年岁小些的男娃娃没过一会儿就开始流泪,哭出了声。男娃也想哭,强忍着不吭声“虽说心中有团火,心中还有家啊。”
大家伙儿低声安慰着哭出声的小男娃,也慰籍着自个儿的心,给自个儿打气。去了上海究竟干些什么,众人都没个谱,男娃跟他们一样没谱“就是想去干点儿啥,不能就这么活着。”
前面的路上有什么,一群未经多少世事的学生娃娃也很茫然。男娃心中很迷茫,他在心里不停地给自个儿打气“心中总有一股憋着的火,需要释放,需要宣泄,哪怕将自个儿焚烧殆尽。年少不轻狂,不做点儿想做的事情,那还叫青春少年吗。”
下车上了去往上海的轮船,找到舱位,放好行李包袱,男娃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没出什么岔子,顺利上船啦。”
这次去上海,几个人都没跟家里说,都是拿了点财物衣裳偷偷溜出来的。众人聚在一起商量,下船以后干点儿啥。汪乔山说话了,男娃晓得他就是这次翘家行动行动的组织者“戴着眼镜,面容白皙,一付很有学问的样子,天津卫本地人,海涛说他挺好的,他心里应该有数吧。”
汪乔山叫大家先听他说几句“大家这次都是第一次离家去上海,没人领着,人生地不熟,最好住在一起,也好彼此有个照应。去了上海,咱们先找地方安顿下来,每天晚上聚一聚,说说各自的想法,什么事儿都商量着办,去了不要着急忙慌出了岔子。一个人出门小心些,安全最重要,出了事儿跟家里没法交待。”
一群男娃娃说没什么不同意见,只是七嘴八舌乱扯了一通各自的想法。
男娃没多说什么,虽然晓得自个儿还是个小娃娃,可他也有自个儿的想法“婆姨都怀上了,我也不能算娃娃了。起码是个小后生,对,就是小后生,顶天立地可以干大事的小后生。去了上海,找找榆生。榆生是自家人,毕竟也姓刘。虽说榆生只在家里见过几面,是爹派去上海揽生活、做买卖的,毕竟大几岁,在上海人头熟。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找他打问打问情况肯定能行。瞅着榆生精干壮实,心眼实诚,跟自己也能说得来,没可能向老爹告密吧,但愿吧。就算叫爹晓得了,想把我抓回去,那也需要不短的时间,上海离镇北多远呀。”
男娃一边心里盘算打划着,一边听着众人说话。男娃瞅了身边坐着的那个脸色黝黑的男娃一眼“海涛跟我算是最要好的,也说得来,这次就是被海涛鼓动来的,我可全听他的,看他咋说。”
海涛听了半会儿,想了想站起来说“同学们,听我说几句。大家都是第一次去上海,上海是个大地方,十里洋场,繁华热闹。我准备先去找找相熟的老乡,打听打听局势和消息,谋定而后动。如果有可能,我想去当兵,为家国出一份力。上海洋人多,规矩大,大家伙儿都小心些,不要惹上麻烦。出门的时候,最好几个人相跟上,别独来独往。真的有麻烦,第一时间通知我跟老汪,大家伙儿商量着解决。大家伙儿彼此照应着,我们也算得上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好兄弟了。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众人听了心里踏实了许多,都不吭声,舱室里一片安静,不一会儿就累了,躺回各自的铺位上。
男娃躺在铺上睡不着,翻过身隐约瞅见海涛在黑暗中闪烁的眼睛,好象也没睡着,睁着眼睛呆,就低声跟海涛拉话“哥,我到上海安顿下,准备找家里人打问打问情况再说。你跟我相跟着行不,咱俩也好有个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