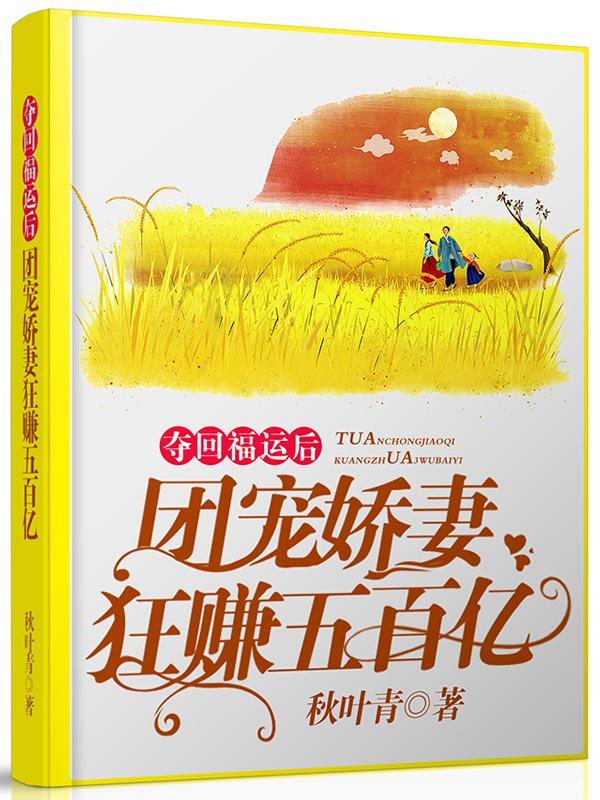69书吧>拖儿带女去逃荒相似文 > 第250页(第1页)
第250页(第1页)
“那海家……”
当初他扳倒了礼部侍郎海百川,众人皆以为皇上听从豫王的话,他十有七八会是未来的储君人选,连他自己都这样认为。
傅景胤轻蔑一笑,说道:“你没读过书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海百川是父皇要留给太子哥的国之重臣,不磨砺一番如何得用?”
豫王再也经受不住,两眼一翻向后倒去。
傅建寅再也不敢装死,连滚带爬地扑了过来:“父王,父王你醒醒啊!您要有什么事,我可怎么办啊……”
豫王妃已经死了,如果豫王也没了,傅建寅就彻底完了。
在儿子的哀声呼唤之下,豫王总算重睁开了眼睛。
只是他连话都没说出来,便狂喷出一大口鲜血。
傅景胤站得稍远一些,从怀中掏出一个黄色卷轴来。
“这是父皇密旨,将豫王褫夺封号,贬为庶民,即日押解朝鲜巨济岛看管,子子孙孙永不许入大宁国境。”
云初知道朝鲜在哪,却不知道巨济岛是什么地方。
可是一听说要被押去朝鲜,傅建寅就被吓得面如土色。
“朝鲜?!为何要去朝鲜?那里离京城足有数千里之遥,而且缺衣少食,住的都是贱民……”
傅景胤淡淡地说道:“看在叔侄一场的份上,我提醒你一句,到那边可别满口贱民的说人家,免得被打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云初在脑海中搜寻着原身仅存的记忆,才依稀记得如今朝鲜已是大宁朝的藩国,那里路途遥远,环境恶劣,除非是犯了谋逆大罪,极少会被流放到那里去的。
傅景胤收好密旨,神情淡然地说道:“父皇顾及父子之情,并未将此事大肆宣扬,待你走后,父皇会说你们一家染了疫病不幸身亡,你的衣冠冢也会入皇陵,你放心地去吧。”
豫王满前襟都是星星点点的鲜血,直愣愣看着傅景胤说不出话来。
豫王再没看他,也未理会苦苦哀告求饶的傅建寅,转身走出了屋子。
云初离开之前,回头看了一眼豫王父子。
她想起一句话,人的欲望就像高山滚石一眼,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就连自己也控制不了,豫王便是如此,他不曾控制过自己的欲望,甚至放纵自己的贪念,结果却被自己滚下来的巨石碾压得粉身碎骨。
傅景胤说是皇上有意纵容,可若不是豫王从一开始就存了不该有的心思,又何至于到这一步?
而皇帝,为了江山,就连偏爱了数十年的女子和儿子也可以舍弃,这就是帝王的无情之处。
云初只觉得心冷如冰,她没有再看豫王父子,抬脚离开了小院。
外面依然艳阳高照,云初却觉得浑身冷,鼻端似乎还萦绕着那屋子里腐朽的气息。
亲眼目睹了豫王父子的惨状,她离开京城的心思越迫切。
一路走出来,两人各怀心思,默默无语。
傅景胤似乎知道她心情不好,什么话都没说,只送她到海府门口,连马车都没下,便道别离去了。
云初怔怔地站了片刻,望着马车离去的背影,只觉得心里百味杂陈。
或许,这是她见到傅景胤的最后一面了。
虽然他曾提起过会去定阳看她,可如果皇上真的时日无多,只怕他一时半会儿都不会离开京城。
待到下次相见,时过境迁,彼此又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了。
云初进了海府,径直回了自己的院子。
宋王氏已经回来了,见她独自回来顿时喜出望外,问了几句诸如他们去了何处,相处如何的话,云初实在没心情回答,借口累了便回房躺下了。
宋王氏见她心情不好,便识地不来打扰,张罗着装糕点收拾行李去了。
转眼到了清明节,因为海百川重起复,海大夫人极为重视这次祭祖,早几日就拘了一家人吃斋沐浴,连几个小的偶尔高声说笑都会被斥责。
到了清明节这日,全家人早早起来,换上或黑色或青色等没有刺绣花纹的衣裳,海大夫人等女眷则用银簪玉饰等物梳挽髻,一家人去了祠堂。
祠堂早已打扫得十分干净整洁,海百川亲手开了门,带海晏清等几个儿子将香烛纸钱,果子糕点等供品进了祠堂。
海大夫人则带了云初几人立在院中,随着海百川举行祭祖仪式,跟着跪下叩拜。
云初还是第一次见识古代的祭祖仪式,见海百川在祠堂内带着男丁跪拜、燃烛、上香之后,又念起了捧起一卷纸张读起了祝文,云初听他念了“天地悠悠,乾坤郎朗,泱泱海氏,源远流长,列祖列宗,德业辉煌……”
之类的一大篇,大概意思是感谢祖宗,请祖宗保佑海家子孙繁茂,兴盛昌宁。
祝文念过之后,又有各种仪式,如孝男行食礼,孝孙行亚献礼,海大夫人也要进祠堂,行供茶礼。
一番繁琐的仪式做完,最后焚纸焚祝文,众人跪拜四叩,才算是礼成。
从祠堂里出来,海百川脸上流露出几分疲惫之色。
他看到院内带着云锦等人的云初,便缓缓走了过来。
“你的事,你母亲都跟我说了……”
海百川望着面容沉静的长女,神情既愧疚又惋惜,“父亲亏欠你良多,只盼望你能一生平安顺遂,日后你想做什么,都随你心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