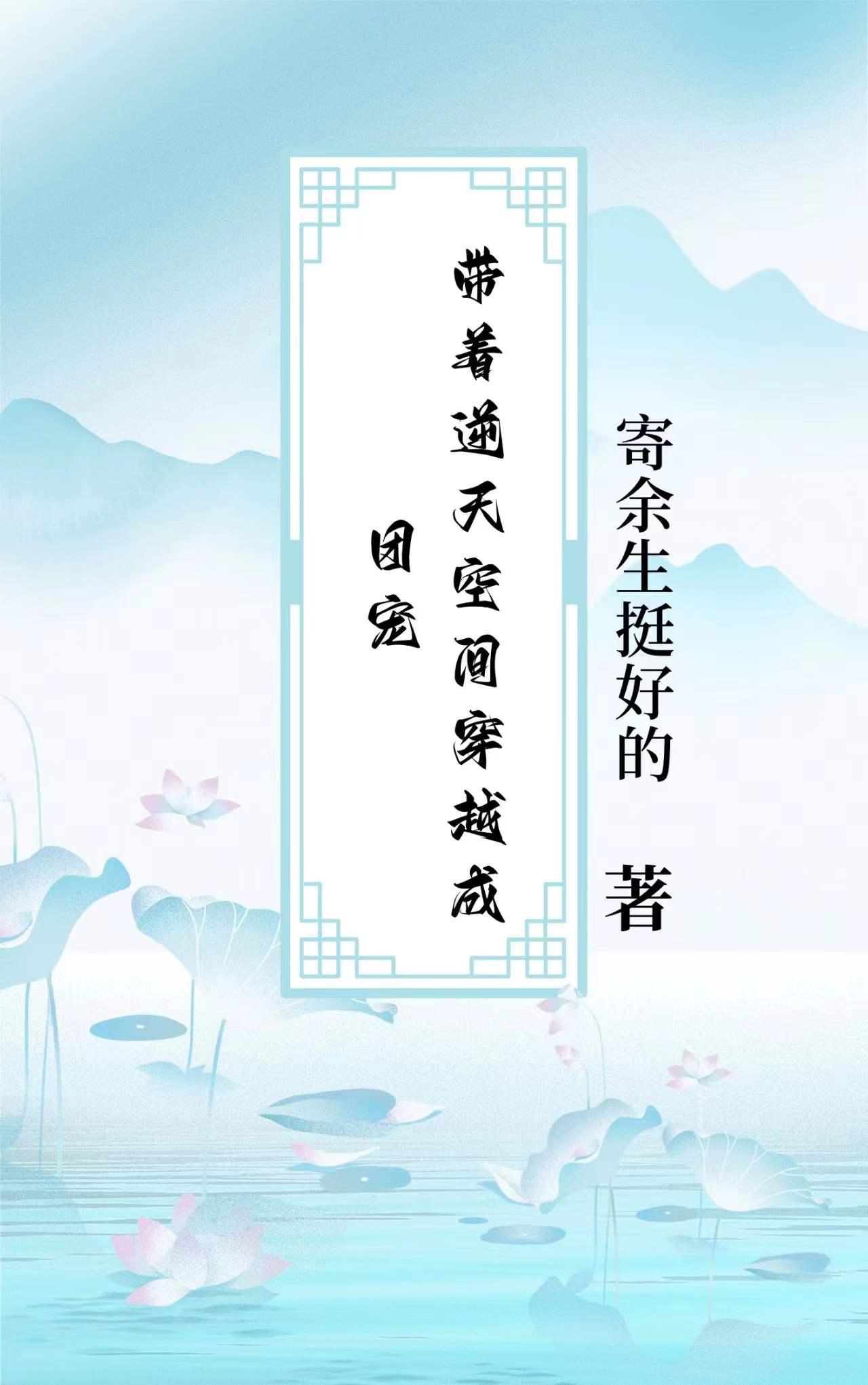69书吧>给前任他叔冲喜 > 第26节(第2页)
第26节(第2页)
“你穿这身是要去哪儿啊?”
月陇西好奇地问。他想到了采沧畔,又不太确定。毕竟如今的采沧畔并不歧视女子,她没必要换男装。就算是从前,她也是光明正大地着女装去的,不曾掩饰过身份。
卿如是躲过他,下意识护了护藏在怀里的面具,“不想告诉你。”
一溜烟跑了。
月陇西挑眉,驻足在原地望着她的背影许久,最后低笑了声。
她取出面具戴上,从密道进入采沧畔时方至辰时。来得太早,叶渠刚起身,小厮让她在房中等候。
桌上已不像前几日来的时候那般凌乱,原先摆放得遍处皆是的书本字画全都收好了。
卿如是有些疑惑,难道这短短几日里,叶渠就找到修复者了?
铺纸,她开始默写最后两篇文章。等她默完文章,叶渠也走了进来。
写下字条递给他:那日,你看的画呢?比对出画的主人是谁了吗?
叶渠想了想,缓缓摇头,“画我借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回来。我比对了许多名仕作品,也没能找到同样的字迹。这下麻烦,怕是没法再重新寻到线索。”
卿如是一怔,随即又觉得这个结果不算出乎预料。
那天她看过画后就隐约有了判断。她从前没少观摩字帖名画,记忆力又不错,那幅画上的字迹她却毫无印象,百年前尚且没见过这字迹,要在百年之后从她没看过的字帖名画中找出那幅画的主人,更是难上加难。
卿如是又写下一张字条:无碍,我不急。默好的《论月》我给你放在桌上的,下回若还能找到需要修复的崇文原作,记得告诉我。
不急二字,说是这么说,叶渠却能看得出她的失落。
他笑了笑,拍着卿如是的肩膀,“云谲的事还多亏了你。贵人已将《论月》找了回来。”
卿如是松了口气,随即又狐疑:那云谲是什么人,查清了吗?为何要盗走《论月》,又堂而皇之拿出来显摆?
叶渠摇头,“那晚云谲单独和贵人在房中相见,我不清楚事情始末。倒是贵人走后,我和云谲搭上几句话。他对我说了些话,我觉得,他很不简单。”
“他说:‘您知道大女帝为何将采沧畔交给您吗?因为她早就料到,女权的气数不会太久,而彼时举朝上下,唯有您能有本事保住采沧畔,并将其发扬。事实证明她料得很准,您为了采沧畔,甚至不惜背上叛贼的骂名,努力地活了这么久。可您终究是不敢踏出采沧畔,那是因为,背上骂名不可怕,可怕的是千夫所指。我说得可对?’”
这话无疑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云谲清楚地知道采沧畔主人是叶渠,清楚知道叶渠的过往。第二,云谲在洞察叶渠的心理,他对叶渠足不出户有诸多猜测,这番话是验证他自己洞察得正确与否。
卿如是沉吟片刻,越琢磨,神情就越严峻,她写道:这人知道你的身份,是你对他说的?还是那位贵人对他说的?
叶渠摇头,“贵人不会将我的信息告诉他人,我的话,只会将自己的身份告诉我愿意结识的人。细想一番,云谲能知道我的身份,还能在我手底将《论月》偷梁换柱,委实不简单。”
卿如是点头,写下字条叮嘱他定要提高警惕,莫要被有心人陷害。
叶渠心底明白,因着贵人的关系云谲实则并不会伤害自己,但依旧笑着点头,宽她的心。
为避免回府太早,她留在采沧畔里看书。
叶渠也没别的爱好,和崇文有些像,喜欢看书和收藏字画,屋子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籍。而书籍中最多的当要数史书。
随意挑拣了一本,竟是记载月氏家族的。
卿如是:“……”
她正想要默默放回去,被走过来的叶渠看见,瞄了一眼书封,笑说,“这册有意思,也是那位贵人拿来给我看的,记载了些外面许多人不知道的事。书不厚,大部分写的都是惠帝时期月氏的兴衰。你一定知道,那个时期是月氏最鼎盛的时期,可你知不知道,那时期也是月家人出仕者最少的时期。”
卿如是微皱了下眉,仔细回想一番,缓缓摇头。
叶渠笑了笑,拈着胡须接着道,“不知道罢?那个时候月氏最有声望的便是月一鸣,惠帝信任他,将大权交到他的手中。他身上背负着整个月氏,实属不易。最后能跟各长老带领着月氏渡过女帝改朝换代这一危机,已是极了不起。大女帝曾亲自请他入新朝为官,依旧以相位待之,被他婉拒。这本书里,月家的人写他是为了整个家族的信仰,才放弃了投靠女帝。我以前也这么觉得,但自打前段时间知道了些……”
他想说秘辛,又思及这事不能外传,于是忍了忍终是没说。
只笑道,“反正,月家的人把话说得好听,真相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没准,他只是被一些事磋磨累了。可惜,月一鸣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大女帝还亲临月氏为他吊唁。我为官那会,女帝上了些年纪,爱絮叨,常和我说起月一鸣。说他,是个命苦的人。从前我觉得他锦衣玉食,年少有为羡煞雁塔,有什么苦的?现在我想想,锦衣玉食,却是真苦。”
卿如是震惊地望着他。
来到晟朝后她还从未看过有关于月家的史料,她一直以为月一鸣是寿终正寝,没成想是英年早逝。最令她惊讶的是,大女帝自降身份去为月一鸣吊唁?去为崇尚男尊女卑的月家人吊唁?
为什么?
看出她的疑惑,叶渠道,“大女帝曾对我说:月一鸣这人分明是反骨头,却又要教他生来就背负家族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