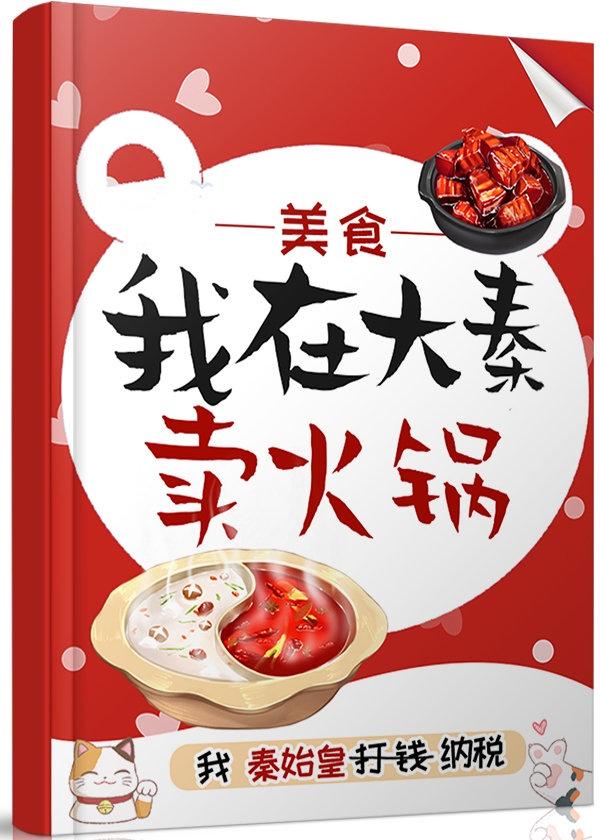69书吧>昨夜星辰昨夜风2免费阅读 > 第1页(第2页)
第1页(第2页)
温若云有著一副好相貌,俊眉秀目,顾盼生辉,唇色如抹了胭脂一般娇豔,衬著白皙的肤色,尤其豔丽。
高桓闭上眼,一次又一次回味温若云的相貌,希望抓住点什麽。
远处传来打更的声音,夜已深了,静得连门外竹叶摇晃的声响也能听见。
高桓睁开眼,仍然是一无所获。他抬指揉了揉眉心,那个位置早已布满了深深浅浅的坎儿,是一年一年积累下来的,非一朝一夕能平复,他只是象征性地碰了碰,已经是习惯了的动作。
起身,端起烛台走向门口,门刚开,刺骨的夜风就迫不及待地扑向他,像张狂舞爪的噬人魔,将高桓整个儿团住,高桓的衣摆、衣带、黑发都飞舞了起来。
在风猛烈的攻势面前,烛火示弱地缩了缩身子,微弱如豆的火光只照亮了高桓的下巴,五官阴沈得几乎看不见。
高桓抬手以掌挡风,烛火在他的庇护下又活跃了起来,照亮了前路。高桓离开房间,踏上後花园里的青石板路,略有些急地迈著步子,待到他停住脚步,眼前是一座凄清阴冷的宅院。
高桓从怀里掏出一把钥匙,举著烛台,用另一只手摸出宅院门上的大锁,铁链拉扯的声音像凄厉而恐怖的嘶吼,高桓脸上的却是平静无波,他早已经习惯。
开了锁,他推开门,闪身进了宅院。
微弱的烛光仍然照亮了漆黑一片的宅院,很大很阔的院子,却是满地的枯枝败叶,被风一吹便沙沙响,像濒死挣扎的人所发出的,无力的呻吟。
高桓踩著这些枯枝败叶走上房门前的台阶。
房门是没有锁的,轻轻一推便能打开,高桓带来的烛台照亮了屋子,而他身後的院子又恢复了死一般的黑暗。
出乎意料的是,房内与院子大相庭径,干干净净,甚至摆设上也看得出是精心打理过。
一只秀丽的长颈花瓶,一扇远山含黛的屏风,一张桃木梳妆台,一面明亮的铜镜,房内有著清新淡雅的脂粉味儿,应是姑娘的闺房。
但这一目便可了然的房里却不见姑娘的身影。
高桓将烛台放在桌上,淡漠的脸上竟有著笑意。
"
卿儿,我来了。"
他道,却无人应,而他仿佛也不在意,微微笑了笑,既是宠溺又是无奈地道:"
是否怨我来得晚了?"
院子里的风呼呼地吹,高桓似乎听到风里夹杂著叹息,他转身时,适才的温情一扫而光,脸上有著怒意。
"
不准你们管我的事,滚!"
他靠在门边朝院子喊。
风仿佛停了,听不到沙沙声了。
高桓怒意未消,将门重重关上。
"
卿儿,我已经把他们都赶跑了,他们再管不了我们的事。"
他对著屋子里说,脸上又有了笑意。
等了半晌,他无奈地摇摇头,道:"
怕是我惹你生气了,也罢,时候不早了,我回去就是。"
高桓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宅院,细心地锁上大锁,这才安心地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不久,天边慢慢出现了红色的霞光,渐渐地,阴冷的宅院便无所遁形,在晨曦中露出它的原形。
高高的白墙里,一座破旧的宅院迎接著晨光的洗礼,黑青色的瓦片错落地铺在屋顶上,霞光过处,闪著诡异的红光。
银灰色的大锁锁著红色大门,门顶上一块崭新的牌匾写著"
祭卿坊"
。
当打更的声音响起,温若云这才发现自己盯著高桓的房门看了很久。
风吹过,他不由得打了个哆嗦。t
这三月的扬州,夜里的风竟如此冷冽。
温若云想著还是赶紧回房歇下。甫一迈开脚步,忽听得身後"
咿呀"
一声,那是沈重的木门发出的叹息。意识到这是来自哪里的声音,出於本能,他迅速地闪身躲进假山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