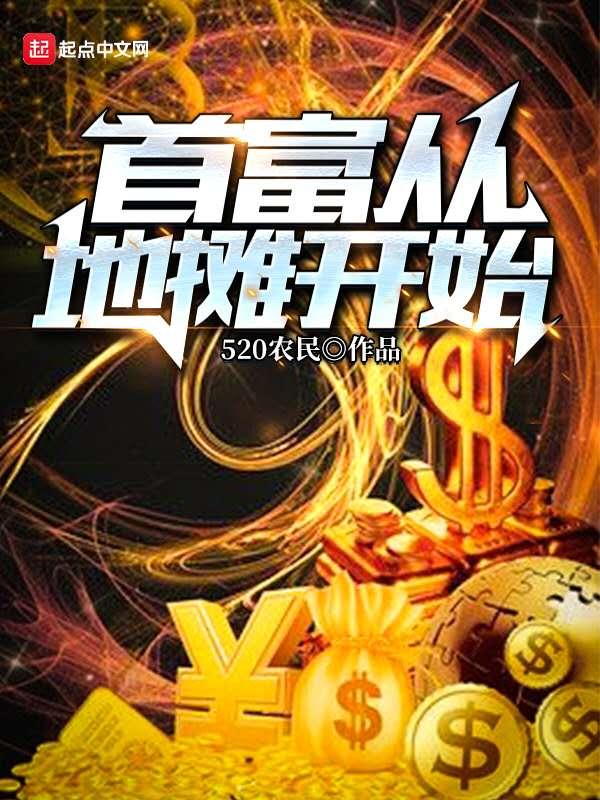69书吧>小美人怀崽后被豪门霸总宠上天 袁舟律 > 第70頁(第1页)
第70頁(第1页)
晏桉是個熱情的孩子,態度忽然這樣,盛懷謙還以為他和溫郁鬧矛盾了,本來還想問問別的,也沒有再問,轉而掛掉了電話。
他除了有晏桉的聯繫方式,還有溫郁另外兩位室友的聯繫方式,即使很擔心自己的孩子也不會像他這樣,溫郁每到一個環境都會加上他的室友同學和老師的聯繫方式。
有時候盛懷謙也會覺得自己對溫郁的掌控欲很強。
給程頤打過去電話,程頤告訴他,溫郁還沒有回宿舍,然後又奇怪地說了一句,「他和我們說晚上不回宿舍,他沒有告訴你嗎?」
不回宿舍回哪裡,以前盛懷謙會以為溫郁住在晏桉家裡,可是他剛剛給晏桉打過電話,晏桉說他不知道。
盛懷謙的笑容止住,「他這段時間還去過外面嗎?」
「這一星期一直在宿舍,上一個星期沒在宿舍的時間比較多。」溫郁不像別的學生,家是外地的,只能寒暑假才能回家,所以溫郁沒回宿舍,他們都默認溫郁回家去住了,不會覺得奇怪。
程頤又想起溫郁最近的異樣,多嘴和盛懷謙說了句,「懷謙哥,你有空帶溫郁去醫院看看吧,他最近可能腸胃不好,總是吐。」
盛懷保持平靜和程頤道了謝,然後掛掉了電話。
夏日的滾熱的風吹過來,盛懷謙站在陽台,心直直地往下沉,他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了解溫郁的人,溫郁到他家後,溫郁做的每一個決定都詢問過他的意見,他參與了溫郁人生中許多重大的決定。
可是現在,溫郁沒有回宿舍,他竟然不知道他去了哪裡,溫郁不舒服了那麼久,他也一點都不知道。
他一時不知道是因為他對溫郁的關注不像以前那麼密切了,還是因為溫郁開始對他有了隱瞞。
一個很壞的猜想冒出來,為什麼要大費周折的給那麼多人打電話,不是應該直接問送溫郁去學校的晏珩山嗎?
為什麼不問他,是因為他和溫郁的身份差距很大,年齡差距很大,又是他們一家的救世主,他將其擺在了高位,認為他對溫郁只是像對待一個晚輩,他自動將他歸於安全的陣營里。
可是現在冷靜下來想想,晏珩山太過於密集,太過於巧合地出現在溫郁的身邊。
想都颱風登6的五天,也是晏珩山接溫郁的電話,那五天溫郁究竟是和晏桉在一起,還是和晏珩山在一起?
盛懷謙想給晏珩山打電話,卻忽然驚覺,現階段他和溫郁接觸的很密切,但他卻從沒有想過留他的聯繫方式。
他又打給了晏桉。
聽到他要晏珩山的聯繫方式,晏桉很直白地愣住了,然後才給他。
記下之後,盛懷謙不急著掛斷電話,而是又問,「小郁颱風那幾天肚子不舒服,一直到現在還沒好,你們那幾天吃了什麼?」
「我不知道,他沒有……」晏桉話說到一半,忽然止住,他反應過來盛懷謙是在套他的話。
而盛懷謙聽到我不知道,便已經知道結果了,他甚至都沒再說一句再見,便啪地掛斷了電話。
然後給晏珩山打過去電話,同樣沒人接。
盛懷謙眼睛浮現出血絲。
孩子大了不再需要父母時,有的父母雖然失望但調整心態後能夠接受,而有的父母卻會極端地將孩子栓在身邊。
他就是後者,他設想的未來生活一定要有溫郁的,他不能接受溫郁和別人組成家庭,不能接受溫郁不再需要他。
他甚至寧願溫郁是個漂亮的痴兒,他會養育他一輩子。
晏衛妄就是在這個時候打電話過來的。
「有空喝一杯嗎?」
盛懷謙冷道:「沒空。」
「我就在你家樓下。」
原本因為溫郁而欲要癲狂的盛懷謙在聽到這句話時微微一愣。
「聽你心情不好,這裡有個免費的垃圾桶,不用一下嗎?」隔著電話,男人漫不經心而又低沉的聲音一字一句地傳進耳朵里,盛懷謙喉結滾動,沒有再拒絕。
兩人相識又不是太熟,對於彼此了解的也並不徹底,對此刻的盛懷謙來說,是一個好的傾訴對象。
他換了鞋子下樓,果真在巷口看見了一輛跑車,車窗落下,晏衛妄英俊的臉龐露出來,朝盛懷謙招手。
晏衛妄也沒想到機會來的這麼快,聽著盛懷謙講述晏珩山他弟弟的事情,他做出一副擔憂的樣子,懇切地望著盛懷謙,那樣子就像他已經完全共情,體會到了他的傷心和憤怒。
而等盛懷謙平靜時刻,他道:「我並不想隱瞞你,其實晏珩山是我哥。」
「他父親和我父親是親兄弟。」
「晏珩山這個人從小性格便有些怪,他父母出車禍意外去世,他卻一直認為是我父親害死了他父母,一直對我們很有敵意。」
晏衛妄拿出手機,給他看照片,照片裡的是李煒,不再是以前囂張跋扈的樣子,而是瘦弱的,頹廢的,一條腿萎縮無力,明顯的殘疾。
「晏珩山做的。」
盛懷謙呼吸微輕,他當然是恨李煒的,可是一個原本健康的人忽然廢掉了一條腿,還是讓他忍不住吃驚,他以為晏珩山只是讓李煒不起訴他,沒想到他做得那麼狠。
「小時候我喜歡和他玩,有一次他帶我去池塘,按著我的頭往水裡按,如果不是家裡的保姆發現……」後面的話晏衛妄不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