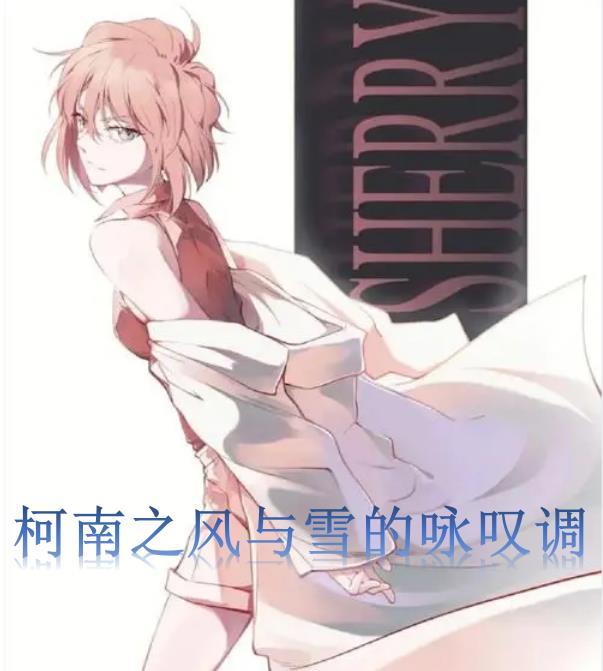69书吧>美人与权臣讲的什么 > 第90页(第2页)
第90页(第2页)
阙扬这般径直说了出来,时也却是听得微怔。
翌国的皇帝年纪稍大,一国皇权更迭,肯定是大事。她一早也在翌国安插了人,但据这几日回报的讯信来看,老皇上也没到崩逝的那个身体地步。
这么一想,时也便皱着脸,带了几分不信任看着阙扬。
阙扬一个摊手,“我也是方才收到的消息,和大人想的差不多,翌国老皇上肯定不是正常的崩逝。但既然就是死了,各方也不可能能去验尸。”
昨夜夜中崩逝,今日便能收到消息。人在西齐,可收到这个消息的度比她还快,“登上皇位的是谁?”
“前阵子,翌国太子便把腿和胸前两根骨头都摔断了,这病根一旦落下。”
阙扬轻捻了下手指。谁登大宝现在还没个确切的着落,但是他心中隐有猜测,“那估摸会是,翌国的五皇子了。”
要让时也来猜,也是会猜的翌国五皇子。
时也扯着垂在她肩上的毛毯子两角,嘴角微挑,“翌国三皇子方才还与你同泡一处温泉池子,你们兄弟情深的,你现在却在这与我畅谈翌国之难?”
“我若是先不和你谈国事,你会停在这里听我说话吗?”
阙扬几次有意跟她示好,她也熟视无睹,只得在这堵着她。
“你知道不会便成,我只对阙国师方才说的走,是去哪儿有些兴。”
毛毯子是他喜欢的水绿色,时也裹在里头只露出了张小脸,衬出了几分平日没有的乖顺柔和。他忍住了想伸手摸摸她头的冲动,低低一笑,“大人,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吗?”
记得,可不就是在边城,那会儿时六被一无赖女子害得险些失了命,雀秧出手相助。尔后雀秧落难,时也还以援手。
想来,不过都是算计,时也懒懒望着他。
他似是知道她心中所想,摇了摇头,“那不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沙场之上。”
“那时我听说西齐让个十几岁的少年郎边城领兵,心下便觉着西齐无人。我与异域的一部领达成协议,我帮他杀了这个少年郎,他予北陇万匹良驹。”
鏖战了大半个月,却未占得这少年郎半分便宜。这少年郎有多狡猾,还撬动了大石部落的人与他们心生间隙,窝里反的,他也在阴沟里翻了船。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她,两人都很狼狈,满沾着泥灰血污,瞧不出本来面貌,只有她那澄澈至真的乌眸看得分明。
“那会儿我手中悄然握着刀刃,你却喂了我一口水,然后走了。”
踩在沙地上孱弱地也随时会倒下的少年,那个纤细却挺直的背影似是火印在心,愈挠就愈深。
时也听着有些抿唇,她当时若知他是北陇国师,估计就一剑下去了。
“时也,我向你道歉。以雀秧身份做的那些事,都是我对不住你。”
阙扬倏而诚恳地在她面前低了头。
无论在北陇还是西齐,低头道歉,是很严肃郑重的礼节,更何况他也是高位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