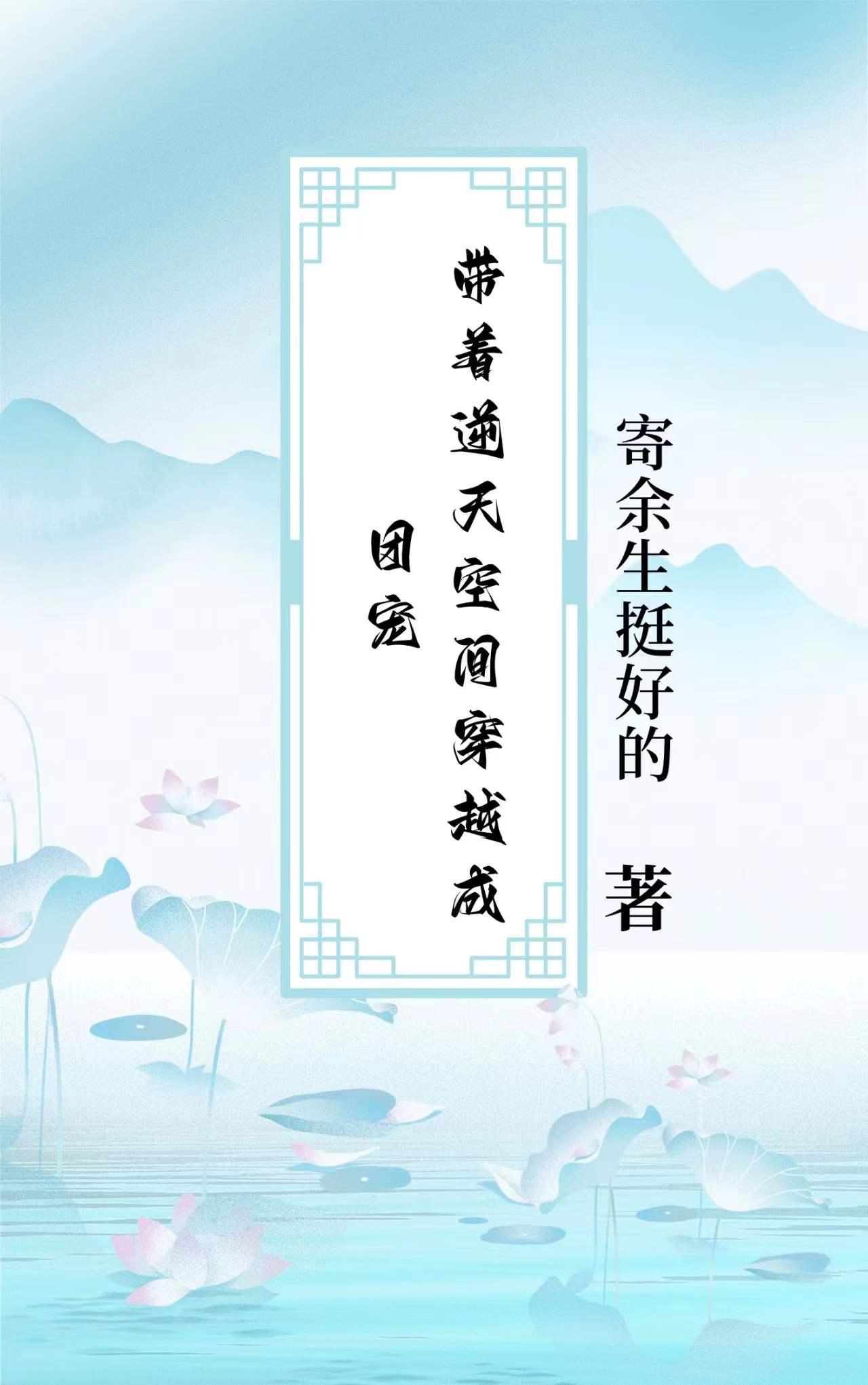69书吧>老爷有喜了全文阅读 > 第71页(第2页)
第71页(第2页)
我站住了脚步,回头看了他半晌,然后缓缓靠近,坐到矮桌对面。刘澈将桌子上的一个黑木匣子推到我跟前,说:“打开吧。”
我游移了半晌,甚至想过——里面装的会不会是蟑螂……咳咳……阿澈又不是我,自然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了。我的指尖碰触到冰凉的匣子,顿了片刻,打开金属扣,翻开了匣子。“这是什么?”
我端详着盒子里的东西,好像是老虎模子?“虎符,兵符,可以调动全国兵力。”
刘澈解释道,又莫名地补充了一句,“只要对方接受调动。”
“只要对方接受调动?”
我摸了摸那虎符,不解地皱眉,“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起当年。皇后虽然手中有虎符,却也调不动我手中的兵,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君王不敢轻易将兵权授予大将,也害怕大将功高震主,威望太高,士兵只认将令,不认君令。”
原来如此。刘澈算是自己起兵逼了宫造了反,便也怕别人如是效仿,就像那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却在后来杯酒释兵权。自己咬了人,也怕被人咬。“你知道,我如今身体状况多有反复,若是一时……便由你执虎符,代我下令。”
刘澈又将盒子推近了几分,说起自己的事,笑得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抓紧了盒子,垂下眼睑沉默了片刻,点点头,收下了盒子。不是矫情的时候,推托只是浪费时间。“希望没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
我低声说了一句。刘澈笑笑,不予置评。一生受宠离开中军帐回自己营帐的时候,陶清与师傅的“男人间的对话”
似乎刚刚接近尾声,我只听到陶清最后一句“……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但真正聪明的人,又怎么会陷自己于死地绝境。我言尽于此,仁至义尽了。”
他抬眼向我看来,唇角一勾,师傅应是察觉了他眼神里的情绪变化,也回过头来,面上神情淡淡,看不出是喜是怒,眼睑一垂,目光闪烁了一下,回陶清一句:“无论如何,拜托你了。”
拜托?我怔了一下:他拜托陶清什么?师傅神色匆匆走开了,我回到陶清身边,把他拽进营帐,立刻盘问:“师傅拜托你什么了?”
他不慌不忙坐下,掸了掸膝盖上或许有的灰尘,仰头微笑问道:“你觉得能是什么?”
我懒得费脑子猜,又问:“你们刚刚说了些什么?跟我有关吗?”
“我说无关你信吗?”
我再问:“你有没有口头上欺负他?”
他一挑眉:“你是觉得我能还是我会?”
我大怒,一拍桌:“陶老二,你这人太不厚道了!”
“哦?”
他对此表示不否认,不过仍是疑惑道,“你是指哪方面?”
我指控他:“你自己问别人问题就要人老实回答,别人问你问题你就一问三反问!”
他这人习惯商业谈判,所谓的公事性对话就是对方问你是谁时你要回答姓名出身,而不能抽象地回答“我是你大爷”
,偏偏我问他问题时,他的回答就跟“我是你大爷”
一样抽象,而且惹人发怒。陶清哈哈一笑,拉着我的手腕引我在他怀里坐下,我象征性地挣扎了两下,抬头怒瞪他。他揉了揉我的脑袋说:“拿他没办法,就拿我出气吗?”
说着拉住我的发尾,轻轻一扯。我抖了一下,立刻知错认错了,陪笑道:“那啥,我不就是一时急火攻心嘛……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计较——你们到底说什么了?”
陶清在我脑门上弹了一下,我哎呀叫了一声,不敢反抗。“不过是战事问题……”
接触到我求知的眼神,他叹了口气,无奈笑道,“是,还提到你了,让我看紧你,别让你乱溜达。”
我听了这话,心里委实不是滋味——他丞相大人便好忙么,还要委托别人监护我。我斜睨陶清。“那你怎么回他的?”
陶清含笑道:“我说,‘我自然会照顾好她,不过与你无关,你也没有立场来委托或者感谢我。’”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陶清,我都不忍心对他说重话,你竟然说了……陶清逼近我,眼中蓄满了意味不明的笑意。“怎么,心疼了?”
我避而不答,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地反问道:“你觉得我该不该心疼?”
“这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会不会’。”
陶清顿了顿,右手食指戳中了我的心口,“不问我,问它。”